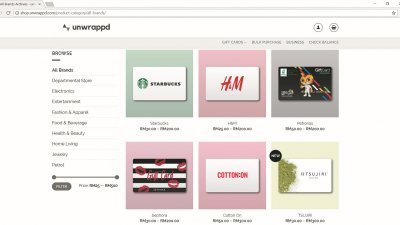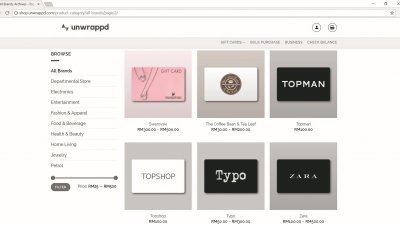拥有“战地玫瑰”之称的张翠容,是华语世界中少见的战地记者,走访过埃及、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东帝汶、科索沃、加萨走廊等动荡地带,对于国际事务有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屡次孤身采访“恐怖分子”头目,却能够自前线全身而退回到香港,“我觉得要怀著这样的一种情怀才有办法走下去,有点像在做傻事,但这个社会需要更多这种会做傻事的人,才会变得更美。”
阔别大马9年,张翠容重新踏足这片土地。受访时,她主动提起与大马的一段渊源。她首个以“独立记者”身份出访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当年安华被革职扣押,掀起烈火莫熄运动,她来马作第一手的观察,并采访了安华太太旺阿兹莎。“那篇报导在香港被人批评写得很幼稚,让我难过了一个晚上。”现在说起来语气还是酸溜溜,然而不服输的她没有打退堂鼓,反而继续前进东帝汶,誓要让大家刮目相看。
1998年,张翠容递上辞呈离开服务的媒体机构,决心当个不依附任何媒体机构的独立记者。她曾在香港的报馆和周刊跑政治新闻,“就是负责跑立法会或香港对外事务采访,真的很闷!”当年老总不时经过她的座位瞄到她的电脑荧幕都会跟其他同事说,张翠容又在浏览与日报或周刊内容无关的资料了,“我感觉他应该是想炒掉我了。”

亲临现场 走近真相
后来张翠容去应征某电台的国际新闻组,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回音,她便主动拨电询问,不料主管傲慢回应:“有结果自然会通知你。”她一气之下,决定不干了,“与其等著被派出去,倒不如自己派自己出去。”当年愿意当独立记者的人很少,因为经常游走在高风险地区,回报却不高。但她希望亲历现场,跟西方记者平起平坐,“我觉得亚洲记者也有能力去到现场,大家有自己的观察,我们不需要依靠西方记者的视野来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据她多年的观察,亚洲地区很少派记者到前线采访,除了日本。
言谈中,张翠容时常咧嘴开怀大笑,颇有傻大姐风范,被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称为“具有正义感的傻大姐观察家”,也被台湾作家南方朔称为“改变21世纪的奇女子”。这位“傻大姐”有她的坚持,认为亲历现场对记者而言十分重要,“如果一个不愿意到现场的媒体工作者,只管坐在报馆翻译稿件,或是看了其他媒体的报导后作评论,我觉得这是懒惰的,也是有所欠缺的。”
张翠容认同人在现场未必知道真相,“但起码我慢慢接近(真相),而且你会发现自己看到很多不同层次的东西。”她说自己不是只深入战地,她行走到欧亚地区、拉丁美洲等地,“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真相就像魔笛
张翠容曾指出,近年来大媒体已不愿派自家记者到战争前线,改为特约独立记者,也因此,大部分在战场上遇害的都是特约记者。人们不禁在问,为何这些记者在亳无保障下,愿意以身犯险?
张翠容以第一位被“伊斯兰国”斩首的美国记者弗利(James Foley)为例,尝试说明这类记者的心态。“弗利曾公开说,他心里就好像有一支魔笛,不时吹奏起来,让他不禁又回到中东地区去犯险。很多记者都说,犯险是为了寻找真相,但真相本身就是一支魔笛,当你尝试到寻获真相的滋味,就会成瘾,不惜一切,务要解开“谜底”。张翠容在香港总是“坐不住”,看到新闻就想跑往现场。“我的朋友们取笑我,血液里头有记者基因。”
作为香港唯一“战地女记者”,张翠容认为,在前线男女平等,尤其是在抢新闻的时候,大家都顾不上男女之分,也不会怜香惜玉。她也不否认,女记者有许多需要顾忌的地方,“我们也怕被绑架,被抓去当山寨夫人怎么办?”另一方面,女记者也有优势,“比方说,很多时候我故意穿长裙,让自己看起来比较不具攻击性。”
眼泪的力量
某次,张翠容的镜头拍下了以军打人的画面,对方威胁她交出录影带。“我跟他说有合法的采访许可证,可是那个场合不会理会所谓的新闻自由,他把M16步枪瞄向我,突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哭了,吸引人路人伫立而望,纷纷指说他欺负女人,那位军人怕事情闹大便放我走。”张翠容语气调皮说:“哭泣是女性的权利。如果换成男记者,可能就无法轻易脱身了。”
现场冲击 心底留下创痕
走过那么多烽火之地,最令张翠容难忘的是阿富汗,“我几乎天天在哭。”会去阿富汗,是因为在网上看见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妇女身上罩了一件“波卡”(burqa),连双眼也被网纱遮盖住,令她大为震撼。张翠容觉得十八层地狱不足以形容当地的情况,“简直像被打入第二十层地狱。”她在现场目光所及处处颓桓败瓦,很少人在街上走动。
她探访当地一所被炸毁的学校。“翻译跟我说,当时学生们坐在教室里上课,一个炸弹投下来全死了。我看见黑板上的粉笔字,知道学生们在上著数学课。”现场的巨大冲击,让她萌生退意。“我的法国女记者朋友因承受不住这种心理创伤,回到法国后,从国际新闻组换至采访时装,喝喝咖啡、看看时装秀轻松多了。”
后来,张翠容在喀布尔大学遇到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她修读新闻系,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看起来很优秀。”这让当时的张翠容感到难以置信,“在塔利班政权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她怎么跑去修读新闻系?原来她期盼国家有一天可以迎来改变,到时候她可以发挥角色。”
“她还反问我,能不能想像,一个没有记者的社会,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句话说到张翠容心坎里去,并且时刻以此提醒自己,“这句话让我一直在反省,记者的角色是怎么一回事,这份工作不是猎奇,不能够看到自己不喜欢的就负气不看了。”
走过无数战火蹂躏下的现场,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听众,她既坚强又脆弱,她眼见耳闻战争底下的悲惨故事,类似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揪心,她坦言自己也有创伤后遗症,“我心里有一条伤痕,触动到的时候会哭不个停。”静坐是她自我疗愈的方式之一。
“我发现自己如此伤心,是因为无法为当地人做些什么,我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感。但是另一方面,我知道记者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社工或慈善家,我们只有一支笔,将他们(当地人)的声音带出来已经很足够了。正如那位女学生说的,这个社会有好记者才会进步。”

真是为凭 不预设立场
现代世界的问题症结是什么,张翠容给出的答案是:殖民主义。“除了二战前赤裸裸的占领,还有无形的殖民,即在背后找个代言人,而殖民主义又与资本主义相关联。”
说到这, 张翠容招牌式大笑响起: “对不起,这么说好像很左翼,有些香港人说我是‘左胶’。”然而她开腔平反:“我不是天生左(派),只是很多时候人在现场,带给我很深的感受。我们不应该太快地把人的观点定性下来,一刀切地说这个人左、这个人右。”
记者能够有自己的立场吗?“记者当然有立场,但要看你的立场是建基在意识形态还是事实上。这很重要。”她口中的意识形态就是预设立场,到了现场只看自己爱看的,或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才写。她说自己没有意识形态,人到了现场,慢慢看到很多的事实与真相,“这时我当然有自己的判断,就像巴勒斯坦,真的不能如此围困那一群人,难道那些不是人吗?”
张翠容访问过不少西方世界眼中的“恐怖组织”。在近距离接触后,她发现,除了塔利班,其他人都是知识分子。访问这些原教旨主义组织的领袖时,张翠容习惯穿长袖戴头巾,“但有次访问真主党时,我的头巾戴不好一直滑落,对方得知我不是穆斯林,还反问我为什么戴头巾。你会看到每个组织的文明程度不一,很难一刀切。”

热爱工作 怀抱赤子之心
世人对战地记者有太多浪漫与危险的想像,张翠容至今能够全身而退,自有她的生存之道。战地记者会碰到四面埋伏的危机,最重要是要懂得“执生”。
她说别把事情看得太简单,甚至乎太天真。“人总会一死,如果可以选择,我宁可为自己热爱的工作而死,也不要死在病床上。”
“当你决定当一个独立记者或是战地记者,除了物质欲望不能太高,你最好不要计算付出与回报。我看到很多前线工作者都带著一颗赤子之心。”她每一次的出发,都是怀著接近事实真相,又或是靠近当地人民而去的。
结束大马行程的下一站是东帝汶,把20年前开始当“独立记者”的路线重游一遍。再度重游大马,已经变天,张翠容表示,若有机会,她想采访我国首相马哈迪,听他分析大马在中美大国之间该如何定位,以及马来西亚在伊斯兰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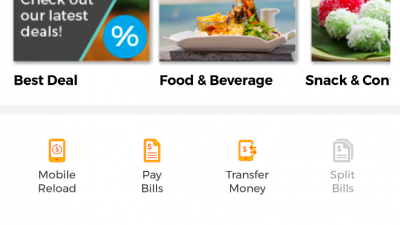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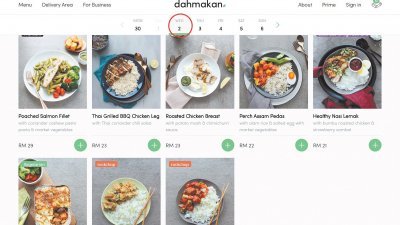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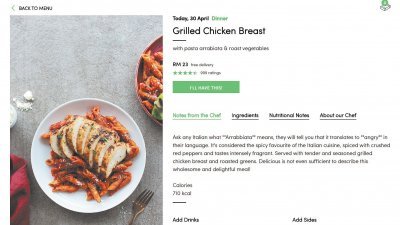






.jpg/131470bdcc84bec2184108dbe8137f5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