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风咳嗽感冒被蚊子咬,对我们来说,是日常生活中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只要到药店购买成药,或是到诊所看医生拿药就可以了。可是,对街友来说,他们要如何到达医院,准时服药、预约复诊、照顾身体整洁等,却是重重难关。
健康照护,在全球讨论中,已被公认为是公共医疗政策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和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以及城市规划是否友善和公平,都会直接影响到街友的生存状态,和健康寿命。
目前,社会福利局关于街友,包括俗称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者、乞讨者的理解相当有限,定义也过于笼统,以至于我们无法更具体地掌握他们的社会处境和生活状态。
而在全国1527名无家可归或乞讨者的街友当中,大部分集中在雪隆一带(628人),在成人分布中,其中以30至39岁占据最多人数,而且男性(923人)远比女性(430人)人数来得高。福利局的数据尚未细致到针对他们的健康作出分析,因此难以让相关组织作进一步的规划,以协助改善街友的生活。
从一个急救箱开始
PERTIWI非政府组织自1960年代末就已开始走入乡区,为女性孩子等偏远乡区的弱势团体提供各种义工服务。随著1970年代的政经变迁,社会经历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城市贫穷成为新兴的社会现象。大约在1999年,PERTIWI开始在秋杰路一带,为性工作者、吸毒者、家庭破碎者或单亲妈妈提供援助。后来因面对志工不足的问题,PERTIWI在2000年离开了秋杰路,直至2010年才重返街头。
这一次,PERTIWI以公益厨房(Soup Kitchen)再度出发,每周数日为吉隆坡市中心的都市贫穷族群,如无家可归者等派饭,一晚大约派出500多个饭盒,至今有7个年头。
虽然早期的PERTIWI也有设立健康医疗服务,但过去是以服务乡区居民为主。2010年,PERTIWI公益厨房到街头派饭时,该组织一开始是担心志工受伤,而特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急救箱。没想到,当志工派饭时,不时有人来问,有班纳杜(Panadol)吗?有虎标万金油吗?PERTIWI公益厨房的急救箱,才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
直到有次,PERTIWI公益厨房主席慕妮拉(Munirah Hamid),接到一位在本地教书的南非印度裔医学专业教授的电话,询问是否可以来这里帮街友看病,街头诊所才正式由此展开。如今,每周会有三天街头义诊服务,分别到吉隆坡城市的不同角落,由两至三名医生值班,这些医生志工分别来自不同专业的注册医生。除了医生志工外,偶有护士志工或医学系学生加入,给街友作些简单医疗护理。

“患上疾病 跟我们一样”
根据其中一名医生志工素加纳(Sujana Muttu)的观察,街友一般会患上的疾病,包括咳嗽、感冒、头疼等,都是属于短期发病,治疗方式也相对简单直接,用药时间也不算长。3年前,他加入PERTIWI医疗服务团队。他也是经友人在不同场合推荐,思考了近半年以后才决定加入。
每个晚上大概会有40到60个街友排队看病,两个医生需要在短短3个小时内看诊完毕。同时,他们还要兼顾到排队看病的街友,是否来得及去另一边排队领取晚餐,以及一些干粮。
PERTIWI从简单的急救箱,慢慢地扩展到有一个人数不多,但长期维持运作的医生志工团队,还有两辆车子改装成流动诊所。可是,PERTIWI资源始终有限,仅能诊断一些基本的疾病症状,为街友提供简单药物。至于那些需要长期接受治疗和服药的街友,则得另作安排。
素加纳指出目前街头诊所的主要困境,“像一些高血压病患跟我们说,我的药物只能用到这个月,你能不能给我下个月的。我们主要是面对运输和供应的问题,没有提供长期药物的条件。”

指引到对的地方
“其实,他们会患上的疾病,我们也有可能会患上的。问题是我们有管道、有金钱,我们可以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如果我们(医生志工)没有出现,他们发烧了要找谁去求助、跟谁那药?”
也是医生志工的庄燕保(Chong Yen Pau)解释,她在2015年年底加入PERTIWI,过去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现在流动的街头诊所。
庄燕保说,那些患有结核病、爱滋病的病患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求助。当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有提供医疗服务时,就会前来看诊。这些病患需要到专科诊所或医院,才能获得适当的治疗,所以,医生志工们就会现场写一封推荐函。
尽管街头诊所无法为患有长期疾病的街友治疗,但是受访的医生志工们认为,至少他们能指引和推荐街友到对的地方,或者是协助进一步的测试诊断。有时候,街友刚好碰到妇产科的医生志工,后者就能为街友提供家庭计划的建议,包括安排对方到他的诊所或医院就医,提供避孕药或荷尔蒙注射等服务。
庄燕保说,有时遇到特殊情况时,医生志工们会立即在群组互通讯息,确认相关专科医生是否能在特定一天来现场义诊,再请街友在指定的时间过来看病。慕妮拉提起,曾经有一名女街友以为自己怀孕,结果志工直接把他送到其中一位医生志工的诊所作详细检查后,才发现她其实是病菌感染。

没有一双好鞋 容易受伤难愈合
在街头诊所现场,医疗护理团队每晚最常处理的工作之一,是包扎伤口。如果未深入理解街友的生活状态,你很难想像他们哪来那么多的伤口。
素加纳说,最简单的因素是:“他们没有一双很好的鞋子。”
街友长时间在都市环境下走动,对双脚是一种耗损,很容易起茧、泡疹或割伤。“当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上我们随手就可以拿药膏来涂,或是用胶布贴住伤口。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选择。”如果本来就患有慢性疾病,如糖尿病,他们的伤口本来就比一般人慢痊愈。
“别忘了他们并没有正规的医疗支援,连平时要控制血糖也非常困难。”素加纳进一步强调。

如何到医院也是问题
医疗支援的缺乏让许多街友患病后,没能及时获得治疗而拖延了痊愈的时机,甚至演变成难以痊愈的长期病状。
慕妮拉发现,街友经常投诉皮肤痕痒,有时候来街头诊所只是要索取一罐虎标万金油防身。有时候他们不断搔痒,结果就造成皮肤破损甚至溃烂。很多街友都感染疥疮,对于一般人而言,这种疾病是能够痊愈的,问题是街友有没有复原的社会条件。
以疥疮为例,我们只要定时涂擦药膏,保持皮肤干爽数小时,隔天定时洗澡维持身体整洁,重复治疗的方式一段时间,疥疮即可病除。庄燕保反问,“问题是,对于街友而言,你要找到一个地方洗澡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的房间,除去衣服涂擦药膏,但是他们要去哪里?”
街友缺乏平等的社会条件,导致身体复原更处弱势。除了没有固定空间可供休息和梳洗外,他们身上没有手机、钟表,难以确认复诊的时间;每天有一餐没一餐的饮食状态,也让他们难以依照医生的指示,在饭前或饭后定时吃药。
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他们要如何从吉隆坡市中心到达中央医院,或指定的专科诊所?
我们或许设想,他们可以搭乘公共巴士,但是有些街友连丁点的车费都没有,甚至一些巴士司机看到他们一身褴褛,也拒绝让他们上车。
慕妮拉补充说:“换言之,诊断和医疗计划只是治疗管理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他们要如何到医院去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尚未包括诊断后的复诊安排要如何处理。”
照顾出院街友 应设后续疗养中心
庄燕保曾经在街头遇过一个女病人,刚开始并不知道她患有末期乳癌,直到检查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她一直都有去政府医院接受治疗。后来,院方跟她说再也没有什么治疗可做了,她才停止去医院。
末期癌症病人到最后,也是处理如何控制疼痛的问题,街头诊所现阶段也只能够提供一些简单的安宁疗护。庄燕保叮嘱这位女病人,若有什么问题或是需要止痛药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找她。若最后阶段需要药剂较重的吗啡,也可推荐她到医院去。
这也牵引出公共医疗资源和社会福利分配的问题:出院后的街友若仍需要一段时间休养身体,他们可以去哪里呢?
尽管慕妮拉认为吉隆坡市政局对街友的态度和处理已有所改善,但是她认为政策依然出现缝隙,“我们有患有大肠癌、中风的街友出院之后就得回到街头。我唯一的希望是政府可以设立后续疗养中心,让出院后的街友可以有一个地方暂时居留,继续休养身体。”
譬如一些患有轻微精神疾病的街友,只要定时用药复诊就能控制病情,并不需要住院或被送到精神病院。可是,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后,谁来观察他们出院后的情况?

临时庇护所功能应细分
社会福利基金(Yayasan Kebajikan Negara)分别在吉隆坡、砂拉越古晋、柔佛新山、槟城设有称为Anjung Singgah的临时庇护所,专门收留无家可归者。但是,非政府组织和街友对这些临时庇护所的褒贬不一,认为其管理条规有待检讨。慕妮拉则认为Anjung Singgah的功能,跟她所建议的后续疗养中心大不相同。
她说,“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街友,对他人造成困扰,有次被吉隆坡市政局抓去,送进医院两个星期后就出院。三个星期药效退了以后,他又打回原形。”
“我们需要一个临时庇护所让街友养病,甚至另外设立一个给精神疾病的街友。”她强调,“每个庇护所的功能都有要个别具体的功能,越具体越特定越好。”
她认为,政府处理在街友庇护所时,应依据吸毒者、精神疾病、一般街友等不同类型,来区分庇护所的不同目的,以给予更针对性的服务。
暂且不谈庇护所是否充裕,或是庇护所的类型是否符合不同类型街友的需求,单看社会福利局所整理的数据,目前仅以州属、性别、年龄、族群分类,并未进一步分析街友的生活状态,包括工作与失业、健康、居住、家人等社会处境。这些数据都会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街友组成的复杂性,也连带影响政策制定者在规划和设立庇护所时,是否能够符合街友的真正需求,协助改善他们的生活。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jpg/410208461f735279f0e6c1129ac1d712.jpg)
.jpg/da47717deb0dfca27f9311194699c72b.jpg)
.jpg/45fc906e440dae27fb8bcb1bab71082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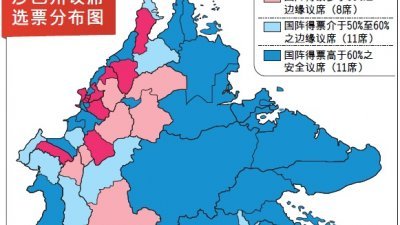

.jpg/c4a1f0ece04cd1f6d379c9b25afc89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