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槟城18岁的印裔少年纳文长期因性别气质阴柔被同学讥笑为“娘娘腔”,毕业后在校园外与前同学起口角,后来演变成围殴事件而导致纳文死亡。新闻出来之后引起一片哗然,纷纷谴责校园霸凌且认为有必要正视问题所在。但翻查与校园纪律相关的官方文件时,发现原来所谓“娘娘腔”,与吸毒、与非法组织及携带枪械或危险物品同罪。
学校作为一个教育场所,应该是服膺和复制主流社会的性别观,还是要成为反思性别偏见的现场,让同学在校园不会因为性别差异而受到歧视?
2017年6月,正值18岁的纳文刚考完大马教育文凭(SPM)从学校毕业,等著到吉隆坡一家学院念音乐,以完成他的音乐梦想。这段过渡期间,他到一家购物商场兼职,而事发那天,他的好友接他下班后,两人到汉堡摊买汉堡时,碰巧遇到以前的2位中学同学。纳文因性别气质阴柔被同学讥笑为“娘娘腔”(pondan),双方发生口角,后来另有3名嫌犯加入,演变成围殴事件。嫌犯除了对纳文和其好友拳打脚踢,还拿头盔敲打他们。

担心报复不敢举报
途中,其好友及时逃出,纳文送院就医时,人已经昏迷不醒,院方证实纳文因肛门遭钝物插入致死。警方本以刑事法典148条文(持械暴动)调查此案,随著纳文不幸去世,警方把案件列为刑事法典302条文(谋杀)调查,目前尚等待过堂中。既然有人死了,为了维护司法正义,固然需要有人填命或付出代价。这5名嫌犯过去与死者同住一社区,他们年龄仅仅介于16至20岁。
过去,纳文长期因性别气质处于同学霸凌之中,除了被讥称为“娘娘腔”,还老是被笑为“鸡鸡”(chicken)或“懦夫”。他曾经衣衫褴褛地从学校返家,护子心切的母亲曾亲自到学校警告欺负纳文的同学,但是纳文不希望家人介入太多,尤其是不要让校方知道,担心自己的处境会因此而变得更糟。
受霸凌的同学害怕举报后会更处于弱势,所以不敢举报是常见的情况。这也是为何事发后,发现校方完全没有任何纳文被霸凌的记录。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受访时,证实纳文不曾向校方投诉过,说此案“无从考察”。倘若纳文正如家人所说,长期遭受霸凌难道与他长年相处的同学、老师真的一无所知。对此,张盛闻强调,“如果他是长期被霸凌,我们一定有记录,可是这个案子看起来并非如此。”

这宗不幸事件发生在纳文毕业后,事发地点在校园以外的地方,况且这起案件是一宗涉及伤害他人身体,甚至致死的刑事案,由警方直接介入调查,校方可以做的仅是配合警方调查提供相关讯息。张盛闻解释,“如果他还是我们的学生,他们回到来进行辅导,不过一旦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很难做到再叫家长回来见面,这已不是学校能做到的事了”。
纳文并非首例,2013年一名成绩优秀的独中生疑不堪被讥笑为“娘娘腔”,在放学途中从公寓8楼跳下自杀身亡;2014年一名13岁印裔少年因性别气质阴柔被同学嘲讽,在家中厕所吞服杀虫药而不幸离世。虽然社会逐渐意识到校园霸凌的成因和形式复杂多重,不过类似案例始终多被当作是校园霸凌的其中一宗,却无视校园内部如何复制主流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导致学生之间因性别气质差异而被嘲笑、欺凌。
校规列“娘娘腔”为大过
饶兆颖(执业律师、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副主席)受访时表示,纳文事件传出后,她认为社会应该趁机深刻讨论两个议题。其一,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成长、学校教育,会让这些年轻人会产生如此的暴力行为。其次,为何他们会对一个与他们不同、所谓“娘娘腔”的人看不顺眼,这种憎恨是怎么来的。

她认为,社会一味期待司法单位尽快裁决,并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年轻人的暴力行为,同时强调社会应从修复式正义而非惩罚的观点,关注加害者与受害者及他们家属所需的社会支援。
翻查《1959年教学条规(学校纪律)》(PERATURAN-PERATURAN PELAJARAN(DISIPLIN SEKOLAH)1959),及教育部于2003年发出的规范通令文件(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第7/2003号等相关教育文件时,竟然发现同学若表现“娘娘腔”(berlakuan pondan)原来是大过之一,与吸毒、殴打、参与非法组织及携带枪械或危险物品同罪,轻则可罚三鞭,重则可被停学。倘若连教育部本身所制订的校园条规,都把“娘娘腔”视为一种违反校园条规的一种错误行为,对性别阴柔特质的孩子带有歧视的眼光,这些孩子在具有正当性的权力底下,他们也难以遁逃于同学之间的霸凌之外。
问及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关于教育部如何定义“娘娘腔”,以及他本人对此条规的回应时,他说:“这一条我要去问我们的部门是怎么定义,它可能在指南里面,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至少我上任两年来,没有任何(人)因所谓的‘娘娘腔’而被采取纪律处分。”
推广性别友善校园
诚如纳文母亲的期待,社会要如何防止再有下一个纳文?我们要如何从这些案例中,更深刻地反省校园内部既有性别教育的传统,并不符合现实中的孩子多元性别的表现。提出多元性别教育的可能,让学校可以成为每个能够放心地拥有自己独特个性和性别气质的孩子。资深注册辅导员王妤娴认为,“我们的性别教育一直把人分为男女两种,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性别,而且这个定义是不断变化当中。传统的性别教育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既定的框框中,认识彼此的性别,衹要你不在既有的分类中,你就不是人。”
她说校园霸凌源自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若要杜绝因性别气质差异所引发的校园霸凌,需建立一个性别友善校园的概念,强调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同时尊重他人,是处理我们与他人的冲突和差异的重要方法。这是一项需要校方、家长和孩子多方面共同参的长远的教育工程,可是却是必须开始的工作。
Diversity异样成员张玉姗表示,受害者家属的态度和立场很重要。不过,她明白家长,能够对孩子异于别人的性别气质表示支持和肯定,与家长是否能从社会获得资源对抗主流社会的性别观有密切关系。此外,她认为我们缺乏一个组织去监督和施压政府推动相关议题,虽然按过去经验即使社会反应强烈,法案也未必能推得动。

台湾校园性别暴力案例:叶永鋕事件发酵 促成性别平等教育法
Diversity异样成员蔡持兴认为,我们能以台湾校园性别暴力的叶永鋕事件为借镜。
2000年,叶永鋕才中学三年级。他从小喜欢玩扮家家酒的游戏,也是个会帮妈妈按摩的贴心小孩。他是学校合唱团唯一的男学员,女高音般的声音令老师印象深刻。他长期因性别气质阴柔而被欺凌,同学会强行脱下他的裤子,虽然曾向学校投诉,但情况并未改善。所以他平时不敢上厕所,只好在下课提前几分钟上厕所,或者在上课钟声响后上女厕所等。
事发当天,他如常在音乐课下课前几分钟上厕所,后来发现倒卧在厕所的血泊中,送医后隔天宣告不治。

以社会行动施压
起初,校方和教育部当作是一般学生意外死亡案件处理,后来教育部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成立调查小组,追查其死因是否与其性别特质和校园暴力有关,依序访谈学校行政人员、老师和学生们,当然还包括当时在看精神科的叶妈妈。
经过6年漫长的调查和后续行动,除了成功与非政府组织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合作,出版《拥抱玫瑰少年》一书,作为教育界讨论性别平等教育的重要参考之外;经过多年官司诉讼后,学校三位行政主管被判业务过失,希望教育人员能从中汲取教训。同时,也于2004年促成台湾《两性平等教育法》改为《性别平等教育法》,让台湾教育政策从两性教育延伸到性别多元的教育观。
蔡持兴希望我们能用社会行动的角度来看待纳文事件,一旦发生以后,我们一定要不断发声,向有关单位施压,希望最终促成性别平等教育法,从根本保障所有学生。
校园霸凌是整体社会问题
掌握校园霸凌的学校州属、性别、案件类型、处理方式,甚至包括霸凌案件最原初的分类和记录方式和相关校规文件,有助于我们追踪校园霸凌的现场,并观察校方如何定义和处理校园霸凌的案件。不过,一位不愿具名、在教育前线工作近二十年的前纪律主任提醒,单以校园纪律记录为例,虽然教育部有发出基本指南,但个别校园仍需自行研发一套管理模式,因此记录素质和准确度也会参差不齐,可能会导致教育部最终统计结果失准。
他曾经见证无数老师因缺乏敏感度,而错过阻止霸凌滋生的契机。他认为,校园纪律管理的关键在于,我们要花时间和学生讨论他的纪律问题,如迟到、未交学费,并协助他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体罚是最后手段。
肢体言语霸凌最多
与“校园霸凌层出不穷”的社会观感不同,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一再地强调,依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校园霸凌仅占校园纪律问题的0.06%,而且有下降的趋势。不过,若按照图表所显示,中小学生涉及校园霸凌行为总数逐渐增加,从2014年的2901宗,到2016年的3448宗,其中以肢体、言语为最大宗。至于其中多少涉及性别歧视的案件,则有待说明。
张盛闻指出,为了回应社会对校园纪律问题或霸凌的疑虑,教育部目前推行一些作法,如设立投诉箱、推动爱心学校,鼓励老师与孩子成为朋友,“所有老师都是纪律老师”的概念等。
他认为,“霸凌不是一个校园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整体社会的参与,如在地居民、家教协会、警方、市政局等。
有别以往学校是封闭的概念,“学校现在是开放的,也是社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单位。教育发展大蓝图的第九条,非常清楚地列明,学校需要把其他非政府组织、私人界、父母纳入进来,需要社区当中所有人来参与。”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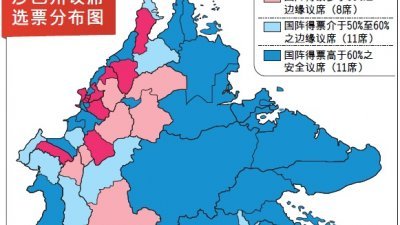

.jpg/c4a1f0ece04cd1f6d379c9b25afc898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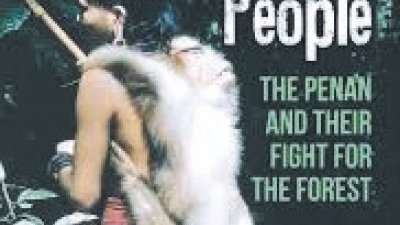



.jpg/37c4c961c711ea241835a10559300496.jpg)
.jpg/bdb07866a9bdda3bca113d097978dfb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