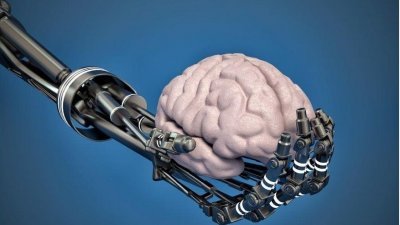现代城市规划的出现,部分缘由出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乡民蜂拥挤到城市谋事,困在拮据的空间;所住之处,多是背背(back-to-back)相依。一切恰如狄更斯的笔记:“这是个最坏的时代。”
磨蹭拖沓,最终钜细靡遗的设计标准,总算逐一提出了,跟著是颁布法令执行之。当年既是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随后采用的规划圭臬,自然不会忽略管制城里的密度。当中,《地方政府法令》第79条阐明:
10岁以上者,应有350平方尺的室内空间。每两位十岁以下的孩童,视同一个成人。倘若违章,地方政府可以拆除。确定违章,既可罚款,或者监禁,甚至两者兼施。第83(2)条文继称:违者每日可罚若干,直至结案。
尽管这样,房屋密度,始终物尽其用。疫情期间,多次突击,点破了一张张的纸窗。2019年5月初那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曾经报告:“雪兰莪敏申组屋、吉隆坡City One大楼,一个单位住上30个人……”
这个画面,自然不限捉襟见肘,钱不够用的外国客工。靠近国家和私立大专院校的“宿舍”,其实也有不少㓥房环滁待租。前面的客厅,甚至后边的厨房,皆改为密不透风,没有窗户的睡房。
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倪可敏要不是孤陋寡闻,否则想必少见多怪,看到一家店屋分隔38间房,因此高调怒斥云云。早在三年前,唐南发兄在〈再谈疫情中的移工群体〉已说:
“我见过最夸张的是30几个人住进一个大约800平方尺的组屋单位,由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轮班制,所以大家按各自的上班时间轮流睡那十几张双层床。……(环境如此)就有几次因为一两个人得了感冒,整个房子的难民集体被传染。”
之所以这样,当然不只是㓥房之过,而是城市的屋价和物价促成。租房平台—iBilik的调查发现,目前有超过600万大马人住在㓥房之中,相等于每十人两位乃是㓥房租户。
甭说类似吉隆坡,寸土如金的都会,小镇之中不过如此的房子,动辄30万令吉了。既然这样,租金自然随之水涨船高。草根市民见之,能省则省,唯有将就将就,寄身㓥房。
倪可敏有心立德立言立功,不妨也研究房价,自可领悟根本玄机所在,何必老是和㓥房过不去?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