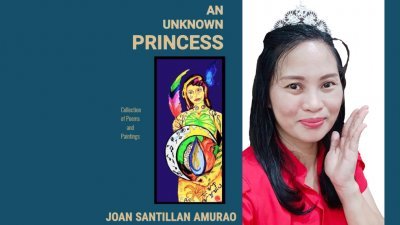“走!去Kapihappys喝咖啡!”Kapihappys不是门店,也不是档口,而是脚车咖啡馆。老板王宝祥每个周末都会把脚车骑到吉隆坡“生命之河”(River of Life)与火车铁路邻近的天桥底下,让客人不时伴住火车的轰隆隆声,品尝一杯精品咖啡,体验不一样的“Café Hopping”(探索咖啡馆)!
采访当天,记者差点儿找不到Kapihappys的所在位置。“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这里虽然偏僻,但风景很好,没有蚊子,还有天桥遮阳。”今年45岁的王宝祥曾当过25年的摄影师,有少许艺术家性格。他此前在郊外岭(Taman Desa)摆档,但人流量非常少。“我带著25公升的水去,至少半桶回来。”

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因为疫情关系“半途出家”,但他说,从2019年就开始骑脚车卖咖啡,但那时只是兼职。因为爱骑车,疫情前,他每周都会从隆市骑到乌鲁冷岳县。“我爱喝手冲咖啡,所以会随身带上器皿。骑完车,喝杯咖啡吹吹风,享受一下风景。”山顶上没有售卖食物、咖啡,让他看准了这个商机,开始边喝边卖。“这场疫情严重打击摄影业界,摄影工作完全停了下来,只好把希望投放在脚车咖啡馆上。”他一周仅营业3天,周末在“生命之河”,星期四则在甘文丁路(Jalan Kamunting)。


摄影酬劳被压榨 对业界感到厌倦
“周末一天能卖出30至40杯咖啡,但遇上下雨天,可能10杯也卖不到。”手冲咖啡的售价介于10至15令吉,王宝祥说:“虽然不用租金,但我咖啡豆的成本很高,不至于赚大钱,但也不会饿死。”他也坦言,这两年确实降低了生活素质,因为过往当摄影师,最高峰月入可达到五位数。

虽然国内的社交活动已经逐步打开,但他认为荣景不复以往,“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习惯线上活动。”当了20年的摄影,他坦言对摄影业已经感到厌倦,“倦”的不是拍照,而是大家都在拼便宜,根本没有意思。“最近一家法国美容公司筹办一场大型活动,需拍摄2天,但只愿付2000令吉。”
商家总会以业务受疫情打击,要求摄影师降价,他认为,这根本就是道德绑架。“活动场地、活动板至少花10万令吉以上,但他们却来压榨摄影师的酬劳。”他直言,即使山穷水尽也不会让步,因为一旦减价,就是不归路。
身为专业摄影师,王宝祥也赞同智能手机总会有一天能够全面取代摄影师。“现在的手机随便拍就很美,当手机能应付夜景拍摄的那一天,我相信很多摄影师都会失业。”虽然收入降低至少一半,但他说,自己算是幸运的,因为无需供房子、车子,大部分收入只用来投资在冲咖啡的工具、脚车和相机上。

长期照护母亲 学会放慢脚步
王宝祥喜欢自由,也喜欢速度。“我以前骑的是公路自行车。”如今咖啡馆用的却是日本邮差脚车。“我原本是买来收藏的,因为它和我小时候骑的脚车很像,所以对它有种特殊的情感。”他说,比起一般的公路自行车,日本邮差脚车有种独特的魅力,但缺点是不能骑太快,也无法承受太重的重量。”如今让他学会放慢脚步的原因,除了疫情,也包括母亲。“妈妈在2019年年尾被诊断患上老人痴呆症,需要长期照护。”
他是家中幼子,上有两个姐姐,虽然一位姐姐还是单身,住在隔壁,但他说:“照顾妈妈的大部分责任落在我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咖啡馆一周只能营业3天。每次出门前,他都必须确保姐姐有空交接照顾妈妈的任务。采访当天,应摄影记者要求,他必须骑著脚车多绕几圈,记者随口说了一句:“实在不好意思。”他却回复:“没关系啊!难得出来,我也是要多绕几圈。”

一个爱自由的人被迫长期困在家中照顾母亲,他坦言真的很辛苦。“患有老人痴呆症的老人其实是很难照顾的,他们晚上会特别活跃,而且经常想获取别人的注意。”他直言,母亲甚至比慈禧太后还要难服侍,因为嘴巴很挑。“她只吃贵的食物,不吃大排档,更不吃我煮的,因为没有味道。”他起初十分迁就母亲,不爱吃就换食物,就怕她会饿著;后来他狠下心,如果母亲不愿吃,就不要吃。“等她饿到受不了时,自然会吃。不然她还没傻,我就已经傻了。”

因为照顾母亲压力大,王宝祥曾经萌生自杀念头。“自杀也是需要勇气啊,我不敢跳下去…”问他为什么不选择把母亲送到疗养院呢?“我有带她去看过,但被骂得很惨。”他分享,自小就在母爱缺失的环境下成长,因为妈妈嗜赌,经常把他丢给保母照顾。“父母因为工作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孩子因为工作无法照顾父母、送往疗养院,就被视为不孝。”他坦言,自己对于这个世俗看法无法理解。“没办法啦,她始终是我的妈妈。”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