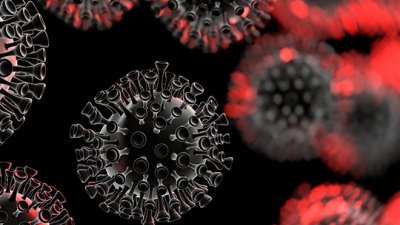邻家曾有只大灰猫,颇为亲人。有时看到人会走过来,却不娇嗲不粘人,祗是张著又大又圆的眼睛,静静地待在一旁,从容而友善。直至某日再看到它,赫然见它瞎了一只眼,下巴也歪了,原来竟遇上车祸。虽然事后养猫人带它去看了兽医,却已治不好这些缺陷。
然而那副从容的派头仍一如既往。有时,在某个宜人的下午,它蹲坐在前院,纹风不动如佛像,一径望向外头,不知是在观察,在沉思,在放空,还是沉浸在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世界。我仔细留意它的表情,脸上却寻不著一丝哀痛或黯然的痕迹,似乎先前的厄运不曾遭遇过。
后来同样的横祸再次降临,这回它没保住性命。
读日本作家佐野洋子的散文,不由得想起这大灰猫,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佐野洋子是绘本画家,画过不少猫,也确实养过一只猫,取名小船。她有篇文叫《普普通通地死》,讲述猫咪生病,她带它去看兽医,照X光发现癌症肿瘤,药石罔效,只好带回家等最后的日子。
濒临死亡的猫咪食不下咽,已无力走到砂盆,但还是会勉强拖著孱弱的躯体走到厕所去小便,它知道那是人类的砂盆。平日,它待在家中一角动也不动,有时悄悄张开眼又闭上,眼里有一种安静的豁达。佐野洋子每日观察它,不禁肃然起敬,心想若是自己,必会呼天抢地地诅咒这份痛苦。她热泪盈眶,打从心里羡慕得以坦然迎接死亡的猫咪。
“尽管人类能登陆月球,却无法像小船一样地死去。正因能登陆月球,所以无法像小船一样死去。”她想,或许只有在遥远的太古年代,人类才能够那样普普通通地死。
人类建构出来的高阶文明,让我们可以恣意享受生之愉悦,却无法直面生命中的破败。就像那只残障又毁容的邻家猫,那劫难若发生在人类身上,恐早已自惭形秽,不能自己吧。但在动物界中,这或许只是日常的一部分。动物没有创造工具,组织文明社会的能力,只靠著原始本能,在天地间的夹缝中求生,命悬于无常的环境变幻中,因而更能直面生老病死,一如叶枯花谢,任由秋风扫落化作泥,再平常不过。
台湾舞蹈家林怀民曾谈起他到印度旅行的经历。他来到恒河边,看到人们焚烧遗体,把骨灰撒到河里。在这不远处,却有人在河里洗澡,喝河水。生和死的仪式都在同一条河中进行,如此自然。这样的场景,或许会让一些外人瞠目,然而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呢?那些我们所不忍直视的污秽或黑暗之物,在某个程度上是否更贴近生命的本源,值得我们去思索领会呢?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