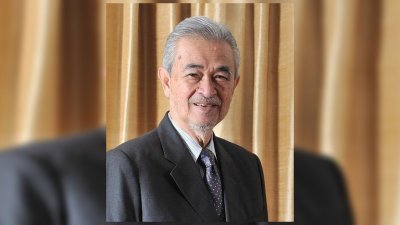每次有外地朋友来槟城,第一句感叹通常不是“风景好美”,而是:“你们的食物好便宜哦!”这句话听久了,我也开始反思,我们槟城的熟食,真的还“便宜”吗?
事先要声明,炒粿条并不在这个课题讨论范围内,因为就算一盘10几令吉的炒粿条也是几口的事,吃的是锅气及旅游的滋味,已不是日常熟食。

先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福建虾面,现在想在槟城吃一碗普通版的虾面,基本行情都落在7至8令吉之间,偶尔还能在某些老社区看到6令吉左右的价格,但那是稀有动物等级的例外了,更别说其他汤面、炒面类几乎也都在这个价位区间徘徊。
吉隆坡的朋友听了会说:“哇,这价钱在吉隆坡吃不到啦,算你们便宜!”但他们一口吃完、坐在那边回神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吃了又不饱,饿又没很饿”的空虚感,才发现原来槟城的熟食没有想像中便宜,便宜的是份量,价钱跟著上了,可满足感却不一定跟得上。
我有一位在槟城与吉隆坡两地工作的朋友就总是说:“吉隆坡虽然东西不便宜,但至少你吃得饱。”他还总结出一个观察:“在吉隆坡,一份云吞面可以让一个人撑四小时;在槟城,要点两份才撑得住。”这话听来有点夸张,但讲出了重点,吃得饱,真的很重要。
尤其对男生来说,在槟城吃面,如果不是点加料版,往往得连吃两碗才有“有底气”的感觉。那你说,这样还能算便宜吗?我看也只是“表面便宜”而已。
当大家还在为“到底是槟城贵还是吉隆坡贵”争论不休的时候,来自新山的朋友就笑了:“你们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是的,南马的物价压力来自另一个方向,因为有个“有钱”的邻居:新加坡。靠近新加坡,就像靠近一台会自动加价的影印机,什么都被影响,什么都“近贵则贵”。
但槟城人就比较憋屈,因为我们的邻居不是富贵型的,而是“便宜型”的,我说的不是吉打,是再往北一点的泰国,人家泰国的物价,简直就是福建人口中常说的“便宜又大块”,大碗又好吃,怎么比?
然而,当我们试著提出这些物价的现象,说一碗面太贵,就总有人跳出来说:“你们不是天天喝十几块的星巴克、手摇奶茶?怎么吃碗面就喊贵?”
这种说法乍听合理,但其实忽略了一个现实差异:星巴克和奶茶,是非必要的“生活选配”;而熟食,是很多人“每天三次、全年无休”的基本需求。更何况,喝星巴克的是“富贵人”和新生代,吃小贩食物的,则是每日为生活奔波的打工族、平民百姓、甚至是退休的阿嬷阿公。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更关注小贩价格,因为这是中下阶层每天生活成本中最直接、最难逃避的一环。如果吃一碗面的成本节节上升,就代表最基层的人要面对最大的压力,这不是在苛责小贩,而是在关注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是否还能稳得住。
我们都知道,小贩也不容易,原材料贵、租金贵、水电贵、人工更贵,这些成本不是他们愿意转嫁,而是不得不算,但问题就在于,当整个社会的食物链,即从种菜、运输到出餐,每一层都在涨,小贩也只能跟著苦撑,那底层消费者呢?他们还吃得起吗?
所以,当我们说“这碗面有点贵”时,说的从来不是对谁有意见,而是对这个时代的无奈,在这个什么都涨,唯独薪水不涨的时代,吃一碗能吃饱、吃得起的面,难道不是我们最基本的愿望吗?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jpeg/cebe8a68101e8ddd4c1c3cb1f1a0284e.jpeg)


.jpeg/01832cd23f4a2fce0dad6bed4a9e7b8b.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