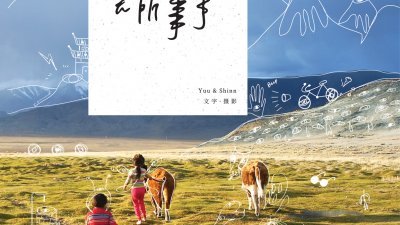懒惰,是大部分人对流浪汉的第一印象,更有甚者抱持他们不愿工作,活该沦落街头的想法,对此,克切拉香积厨项目总监谢国良并不认同。他认为,与其说流浪汉“懒惰”,不如说“自我放弃”更为恰当,他们会流落街头,更多是精神打击所致。
访问开始前,谢国良指向对面在石凳上睡觉的流浪汉问道:“你觉得他是懒惰吗?”记者笑而不语,他续说:“看他全程拿著雨伞遮太阳,一个真正懒惰的人,他们会连雨伞都懒得撑;若真的怕晒,他们也可以到有遮荫的地方,但他却硬要睡那个石凳。或许是他钟情于那个地方,也有可能是他之前面对的事情,让他坚持睡在那张石凳上。”谢国良分享,之前曾接触一名原是会计师的流浪汉,而让他选择流浪街头的原因,是经不起老婆背叛的事实。
同样的,今年60岁,人称“Kak Aisah”(译名:爱莎)是经常穿梭于吉隆坡半山芭一带的露宿者。“我们有一名义工是爱莎的前同事,自爱莎在十多年前离职后,他们就不再见面,但没想到再见面,爱莎就成为了露宿者。”谢国良说。在留宿街头前,爱莎也曾经每日衣著光鲜,在银行任职高级执行员,常有机会到澳洲、日本等国家公干。“东京的治安比吉隆坡好太多了,环境又干净。”和她聊天,发现她会常拿我国的治安和他国相比。

昔日白领 今朝捡纸皮维生
爱莎能说上一口流利的英文,看得出她曾受过教育,但为何最终流落街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在40岁离职了,现在靠拾纸皮为生,收入没办法负担昂贵房租。”那为什么当初要提早离职?这时的她支支吾吾,不愿多谈,只是一味说是职场斗争问题。“所以现在的我,谁也不帮,管好自己就好。”那家人呢?“我有哥哥、侄儿,但哥哥都老了,怎样能照顾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但谢国良说,克切拉香积厨是在2006年开始接触爱莎,也就是说爱莎流浪至今已经至少12年了,而且根据纪录,爱莎曾有过一段婚姻,有儿有女,但她在访谈之中不曾透露自己的婚姻状况。“我们猜测他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而受不了打击,所以才会毅然辞职,自我放弃,流浪街头。”
爱莎目前以拾纸皮为生,每日收入不稳定,有时最高可达60令吉,有时却是零收入。“哪里够租房间?只够吃。”爱莎说,之前她曾在半山芭一带租房间,但后期因为和屋主意见不合,所以宁愿流浪。“她(屋主)一直占我便宜,要在我身上拿到好处!”她气愤地说。她续指,自己也曾经被骗钱。“当初我原是想购买一辆3000令吉的二手车,但没想到对方拿走了我的钱,就不见踪影了。”

缺屏障 常被骚扰欺侮
爱莎是少数的女性露宿者,因为相比起男人,女人睡在街头上更具挑战,因为随时会被外劳侵犯或殴打。爱莎坦言,自己在这段留宿街头的日子确实曾遭外劳殴打。“这世界太多orang jahat(坏人),他们就只会欺负我,还试过拿头盔打我,把我打得头破血流!”她说,露宿者必须学会保护自己,即便她身材瘦弱,但经常都会搬出一副相当强悍模样,希望可以吓唬企图要欺负她的人。
同为露宿者的戴沙盛亦无奈表示,不仅女人会被欺负,就连大男人睡在街头也随时会被殴打。他分享自身经验说道,他之前“住”在秋杰路,但那里比较复杂,晚上有人抽大麻,然后来骚扰别人。最后,他才来到茨场街“留宿”。他感慨:“晚上睡在街边其实很没有安全感,我也怕被打抢,所以很容易被吓醒,要到白天人来人往,更安全时才能睡好。”
爱莎续说,若遇上天气非常炎热,她也会选择在晚上才出动去捡纸皮,早上则选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睡觉休息。“所以流浪汉一般会在晚上才比较活跃。”虽然年届60岁,她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算健康,可自由行走,但眼睛最近似乎患上白内障。她计划近期去进行治疗。

怕羞害己 人多处才安全
爱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新的地点休息、睡觉。“我之前是在银行门口,但因为后来有人喜欢在银行里打架,所以我现在就搬到这里。”见到爱莎时,她是坐在24小时的便利店旁边,隔几间还有一间营业到深夜的粥店。“对我来说,人流多的地方就会比较安全。”她续说,睡街头不能怕羞,如果因为怕羞耻而躲在没人的地方,它会害死你的。她感恩表示,便利店的职员都很好,他们都愿意给予她一些照顾。“当他们有额外的食物时,还会分我吃。”爱莎边说边抚摸身边的猫咪,更不忘向记者介绍,这是她饲养的猫。“它是我在路边捡回来的,如果不收养它,我怕它会被车撞死。”
爱莎的随身物品不多,就一个手推车和一些纸皮。“每天早上我就会把我的物品交托给一个看管停车场的外劳看管,每天3令吉。”她说,之前她只是随意把物品放在楼梯口,但常会被人偷掉,所以她宁愿付钱让人帮忙看管。“不然我的东西可以放哪里?”她无奈道。她一般都到附近的公厕梳洗,但必须很早,以避免被其他人看到,但她也曾试过将近一个星期没有洗澡。“没关系,我都已经习惯了。”她说道。

非“懒惰”可以蔽之 人人都有故事
正如谢国良所言,每个流浪汉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并非“懒惰”两个字就能概括。他分享,曾经有一名流浪汉伯伯在天桥底下住了将近10年,由于他的年纪越来越大,团队便著手替他与老人院接洽,送他到老人院生活。“但他只住了3天,就逃出来,然后继续住在天桥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同样的,另一名流浪汉——戴沙盛并非没有家人,他有老婆、女人,却因为自己在年轻时沉迷赌博而最终落得流落街头。“我生性烂赌,落得如斯下场,怪不了别人。”他续说,当初老婆是没办法忍受他烂赌的缺点,带著女儿离开。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悔改,最终更是交不出房租,被赶了出去,开始露宿街头。
说回爱莎,她曾在银行任职,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巫语,要找一份文书工作想来并不艰难,她却表示:“像我们这种人谁还愿意请?”爱莎告诉记者,自己目前对生活的要求其实不高,只求三餐温饱。“拾纸皮虽然赚不到很多钱,但至少还不会饿死。”
谢国良坦言,爱莎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有时能以正常的思路聊天,有时却会胡言乱语,大骂政治,确实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上周六晚上,记者随著克切拉香积厨团队到半山芭一带帮忙派送食物,发现大部分流浪汉都有属于自己性格和个性,有些流浪汉面对来派饭的义工会连连道谢,有些却完全不愿与他人打交道,若把食物放在他认为不对的地方时,还会破口大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