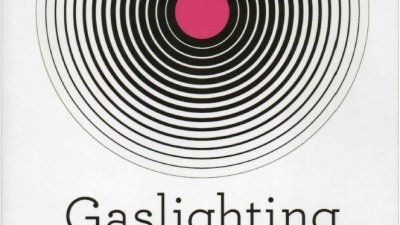吉打首府亚罗士打南边25英里,有一个奇特的村落Kampung Cina,流传一则古老又神秘的传说,这里住著200户约800人口,几乎尽是全盘暹罗化的华民。至奇是,此村形成聚落近300年来,祖辈口头相传的一批开发领袖为明朝末年遗民,首领郑天恩被指或是明末抗清的郑成功之子,他率同其子郑能,以及亲信如管家陆男、武将洪百甫等27人外逃至泰南北大年(Patani),结识了也在北大年避难的吉打王储Tunku Abdullah,并受邀南下吉打落户以在战乱中助一臂之力。
这个村落华民最初依据区名唤作Padang Kerbau,1824年英殖民官员John Anderson记述此地有309间住屋。马来文Kerbau即水牛,1965年黄存燊《华人甲必丹》记之巴东克保,1967年黄尧《马星华人志》记之水牛坡,1993年锺锡金《吉打二千年》记之巴当可包,2005年陈鸿洲《吉打风雨路》记之巴当格茂,资深通讯记者王良记称之巴东各卯,而周边一带华民多唤之“山顶”,暹罗话地名则为同快(Thong Kwai)亦为牛场之意。后来直称Kampung Cina,据说亦采用了上百年,也有人称之甘光支那或甘榜支那,Kampung Cina老村民王福春则唤之“唐人寨”。
吉打暹罗化的华民村落不仅是唐人寨,Kampung Cina北边数公里外的南邦(Lampam)、还有纳卡(Naka)以及纳米(Nami)等地,原来都是暹罗化的华民村落。1912年英文《海峡时报》在一篇人口普查的报道中称,吉打各族群之间的通婚很普遍,后裔甚至以外语替代自己的方言,其时便有638名华民、108名暹罗人及78名印裔不再说自家方言,华民父亲与暹罗母亲生下的孩子,基本上只说暹罗话与马来语,至于有些宁说暹罗话的马来人,也即被称为Samsam的马来人,人数比说暹语的暹罗人更多,而且他们的妻儿一般都忽视马来语。
至1946年英文《海峡时报》又称,吉打所有暹罗人几乎享有与马来人同等的权益,包括保留地也同样开放让他们申请。唐人寨老村民王福春不讳言,暹罗化可享有如土著同等权益,包括他在内的唐人寨华民都选择了入暹。不同的是,王福春曾在亚罗士打受中文教育,虽说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已改为暹名Bon Lua,但只有对外官方用途始采用暹名,日常仍坚持使用祖先的姓氏“王”。王福春既说一口流利华语,也通晓英语、马来语,更说一口流利本土暹罗话,惟移居亚罗士打组织家庭后,下一代虽保留暹名但已不说暹话了。
所谓暹罗化,即口语与风俗,当然也包括宗教(暹佛),均按照暹罗人生活习惯。王良记、王福春皆称,唐人寨与其他暹化的华民村落,主要区别在唐人寨暹化的华民比较多,其他则是原暹罗村民居多。然而王福春告知:“唐人寨仍有原暹罗人,惟如今多已通婚难以区别你我,不过从外貌勉强尚能分辨一二。若以在家文化风俗习惯,过年过节就能一览无遗,暹化华民在外地工作、求学的游子,农历新年、清明扫墓都必定返乡。我有一个堂妹,已皈依穆斯林,也带她的儿女回乡跟我们拜年,这就是唐人寨的特点。”
唐人寨另一奇特的存在,是村里至少出了两位甲必丹,还有另两位传说中的甲必丹。吉打官方记载的兄弟甲必丹李欲修、李欲正便出自唐人寨,两兄弟除中文亦精通马来爪夷文,一被委为苏丹私人秘书,一则为苏丹的财务司,既受苏丹器重亦在官场中享有尊贵地位。笔者不久前到吉打采风,在王良记、王福春等领路下,微雨中在村民的果园实地探寻李欲正之墓,另外在胶林深处亦探寻了李氏兄弟父母李蛋观、洪维登,以及外祖父母洪百甫、林勤俭之墓。笔者并发现,在母亲墓碑上李欲修名字写成“收”。原来漳州话收与修同音,李欲修原名或是李欲收之误?然而,亚罗士打李欲修墓碑上却又作“脩”。
洪百甫墓碑上注明原籍云霄,李蛋观墓碑则注明原籍铁山,这两地皆属福建省漳州府。云霄是天地会起源地,曾是反清复明大本营之一,入会志士大多以洪字为姓参与抗清,职是之故洪百甫或非其真名,但洪百甫看似亦非泛泛之辈,因“百甫”含有第一百名志士之意,王良记推测洪百甫或是习有南少林功夫的武将。洪百甫墓碑志明卒于乾隆庚寅年即1770年,Tunku Abdullah被圈定苏丹继承人后引起多个党派内讧,王良记相信洪百甫在暹罗人趁乱入侵时战死。
1938年生的王良记,母亲郑庄沅汆为郑能幼子郑文璋的外孙女。母亲一辈曾告知先祖口述,郑天恩等是躲避满清皇帝的追杀逃至北大年再转入吉打,母亲生前每次扫墓都会带同王良记等儿孙拜祭郑天恩、郑能等先人,不过他们的坟墓或因身份隐秘,没有立墓碑刻载姓名、原籍地等,母亲仅告知先祖原籍厦门。王良记根据祖辈口传线索,遂推测郑天恩或是化名,很可能即郑成功第六子,原名郑宽,又名哲硕、硕之,约莫1740年代来吉打时已是60出头了。“郑天恩管家叫陆男,陆男也可能是化名,六男,第六男也,那不是暗喻第六子吗?”
根据王良记,郑天恩原墓离唐人寨仅500米,再北边即其子郑能等墓,现其后人迁墓重修,由于暹化不懂中文,墓碑上非但没有中文,即便“郑”姓也没有了,仅志明闽南话发音的Thian In(天恩),以及Anak Lelaki: Pek Leng。然而所谓郑成功六子毕竟离奇且犯驳太多,其一郑成功原籍南安并非厦门;其二依据台湾郑成功后人之说,1683年郑成功第六子即已隐姓埋名于台湾,并育有郑克培;其三郑天恩1740年代来吉打时或是70岁矣,那时候寿命较短即便60出头是否有必要外逃?其四,郑成功10子之中,据记载只有第五子、第九子失踪,完全没有提及第六子下落。
郑天恩身份神秘,其子郑能更是传奇,相传郑能五岁随父来到唐人寨,长大后在助苏丹平乱时救了一名马来女孩,带回领养约莫10年后与女孩成婚,后来的后来始知女孩有王族血统,马来社会便称郑能为Baba Leng(峇峇能),华民则唤之“阿伯能”。祖辈曾告知王良记,郑能与苏丹关系密切,曾受委Kota Setar(今亚罗士打)甲必丹。话说回来,郑能受委甲必丹的传说没有任何佐证,1869年Kota Setar确委有一位甲必丹Ah Seng,但那时郑能超过130岁不可能是同一人!
至传奇也至争议却是1810年代受委Kota Kuala Muda甲必丹的Baba Seng(峇峇成)。峇峇成先是一名剃头匠,后来开设赌场发了财,在他担任甲必丹时公正不阿,对进出Kuala Muda的英国船也照样征税,被英殖民官员标签为blackguard(恶棍之意),后来甚至为他扣上接受赃物、窝藏海盗的罪名,1818年槟榔屿总督Bannerman曾施压吉打将他免职但未成功。暹罗人对峇峇成也没有好感, 1821年暹罗入侵吉打后便把峇峇成关押,但马来社会视峇峇成为英雄,因他协助吉打马来人对抗暹罗,马来学者Mahani Musa相信峇峇成属于包含海山在内的Tua Pek Kong(大伯公会)帮会,而当时亲暹罗的辜国财则属义兴帮会,换言之吉打暹罗之战亦有华民帮会涉及?
峇峇成的原名与出生地没有任何记载,王良记推测有可能是郑能次子郑丁成,因父峇峇能之名遂也被唤作峇峇成,时间点上虽有可能惟同样没有任何佐证。说完一句,唐人寨先人源自明末遗民看似不假,但所谓郑成功第六子、峇峇能及峇峇成父子甲必丹之说,或许有过多戏剧化的想像和臆测?至关键,这批明末遗民来吉打相助对抗暹罗,到最终明末遗民却成了全盘暹罗化,这是历史的玩笑还是历史的荒谬?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