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镇即使建筑林立,不意味著必然是给人安居乐业的地方。宜居条件倘若每况愈下,是有可能变成空有房屋毫无人烟的鬼镇。同样的,一片种满树的土地,不一定是适合繁多物种栖息的森林。
2009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国家实体规划提出中央森林脊柱(Central Forest Spine)概念,主张把西马横跨8州的4片大森林,从柔佛到马泰边界连贯起来,借此保护森林物种依赖的生态环境。
森林里的动物无论是求偶、迁徙、觅食,依赖的是森林地、河流,不是高速公路。即使换作人类,住在一个开门就只见高速公路的地方,一样是百般不便。森林物种的生活环境因著人为开发而受破坏,自然就形成生态剧变,一些物种开始频密接触人类,一些物种则逐渐消失。疾病传播风险也随之增加。这样的森林状态称为碎片化(fragmentation)。
若单纯从树桐采集的角度来看森林,很容易“见桐不见森”,会认为“一样长满树”。这就像一个人眼看自己的肺被切成几十块,却因为总面积依然没改变,而坚称“一样是一块肺”。
在永久森林保留区开垦园丘,因此,完全称不上是护林。
森林屠宰场
所谓森林园丘(forest plantation),就是在特定土地大量种植特定树种,以满足木材市场需求。根据马来西亚木材理事会的说法,其用意是纾减国内森林承受的市场需求压力。以白话来说,森林园丘是原始森林的替身,取代木材来源的角色,从而达到保护森林的目的。
但,森林局网站却把森林园丘列为“森林种类”。
这很有问题。
因为,在森林开拓森林园丘,必须把原本的树都砍光,然后栽种相关树种。这和种植油棕是同样的概念。
马来西亚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Malaysia,SAM)田野调查员米尔拉萨(Meor Razak)解释说,接受在森林地开拓森林园丘,就等于是认同将那里的树木砍光。这种砍个清光的伐木手法,称为“皆伐”(clear-cutting),在马来语还有一个满有画面感的形容:“洗碗”(cuci mangkuk)。这根本就和木材理事会提及的环保理由背道而驰。
“森林就是森林,园丘就是园丘,两者根本就不同。把树砍光了再种植单一种类的树木,这哪算是什么森林?”
因此,大马自然之友不接受“森林园丘”这称谓,坚持称之为单一种植园丘。
“这种园丘若是在森林范围外面,我们不会反对。在森林范围内就绝对不接受。”
根据米尔观察,吉兰丹境内永久森林保留地,种植克隆橡胶木(timber latex clone)的森林园丘占了总面积的27%。这种园丘的面积,动辄至少400公顷。
州政府到底是凭什么理由,把一片森林批准为森林园丘?
“当局的理由,是相关森林已退化成没多少值钱木材的‘贫林’。我问他们森林怎么会变成‘贫林’,毕竟我国气候并非极端到足以造成森林自燃。他们就说是原住民的错。这说法一样不合理。原住民即使是盗伐,顶多只能开发10公顷左右,怎可能把400公顷的森林地带变成‘贫林’?这么大片的‘贫林’,只说明森林局没尽责。”
2020年2月21日,雪兰莪州务大臣解释撤销瓜拉冷岳森林保留区的理由,就提出“贫林”之说。
“霹雳森林局就换了说法,称之为‘次生林’。我说这一样不合理。如果森林局细心经营,次生林也可以恢复成原生林。这一切说辞,根本就不足以将批准森林园丘的理由合理化。”
被惩罚照样赚钱,谁怕?
森林局如果失责,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
各州森林局的表现,其实都须经过木材理事会评估,一旦合格就可获得森林管理认证,木材就可出口到欧洲国家,州政府也因此脸上有光。林务表现方面的监督工作,就由马来西亚工业标准研究院(SIRIM)负责。
“SIRIM的人力有限,无法到处派员突击检查。他们每年都邀请非政府组织给予意见。问题是,你必须获得森林局批准,才可进入永久森林保留区。如果说要爬山、钓鱼,你只需付费就可以进去。我们就说是进去监督,他们不允许。所以,我们只能够针对保留区外面的问题给予意见或投诉,例如罗里违法之类的。森林保留区里发生的事情,只有森林局官员和伐木业者才知道。都不能进去,怎监督?有时候,原住民把违规伐木现场证据拍下传给我们,再由我们向SIRIM投诉。”
尽管占尽不合理优势,有3州的森林局还是丢了管理认证。
2016年1月1日,木材理事会宣布冻结柔佛森林局的森林管理认证。吉兰丹森林局的认证在同年3月18日被冻结,随后在9月23日被撤销。2019年5月8日,吉打州森林局的认证也被冻结。
“没认证就不能把木材卖出国外了,不过依然可以在国内卖。”
这样的惩罚,只足以削减利润,根本就没能力阻止毁林。
米尔认为,若要平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森林事务的权限,也许就得修宪。
“但,有哪个议员愿意在国会提呈这样的动议?修宪降低投票年龄,所有议员都支持。若修宪使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不再坐享绝对林务权力,他们会支持吗?”
修法诚意
采访结束后,和米尔闲谈中提及以内脏比喻森林。他不假思索的说:“砍伐集水区森林简直就是卖肾啊!”
我们告别后的两年内,瘟疫杀入国内,社会各阶层为了保命而学习接受各类防疫措施。但,这些“新常态”,并不包括正视人畜共通病和毁林的关系。当人们开始觉得已经有能力和自信克服瘟疫的时候,那毁林致富旧常态机器也随之复苏,永久森林保留区的幌子就继续受用。
今年3月3日,能源及天然资源部在国会提呈国家森林法令修正案一读。部长达基尤丁表示希望修正案可以在7月国会通过二读三读。然而,这次修法,虽说增添公众意见环节,州政府依然掌握林务绝对大权,环保组织会否获准更积极参与监督依然是未知数。
中央森林脊柱概念至今已有13年,国内毁林依然日趋严重。失控发展衍生的问题,一旦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来解决,往往是拿森林地带开刀。南北大道若再加宽,中央森林脊柱的森林碎片化就更严重,也意味著更剧烈的生态波动。
此次修法,会否是大选前换汤不换药的糖果?这些糖果如果还包括加宽南北大道以解决塞车问题,选民会否联想到森林的命运,以及他们本身在未来疫情的生存本钱?他们是否愿意用选票救森林,从而救自己?
我们之所以保护森林,是因为我们需要森林的保护。
眼前疫情还未离我们而去。若要避免再点燃瘟疫导火线,请学习重视护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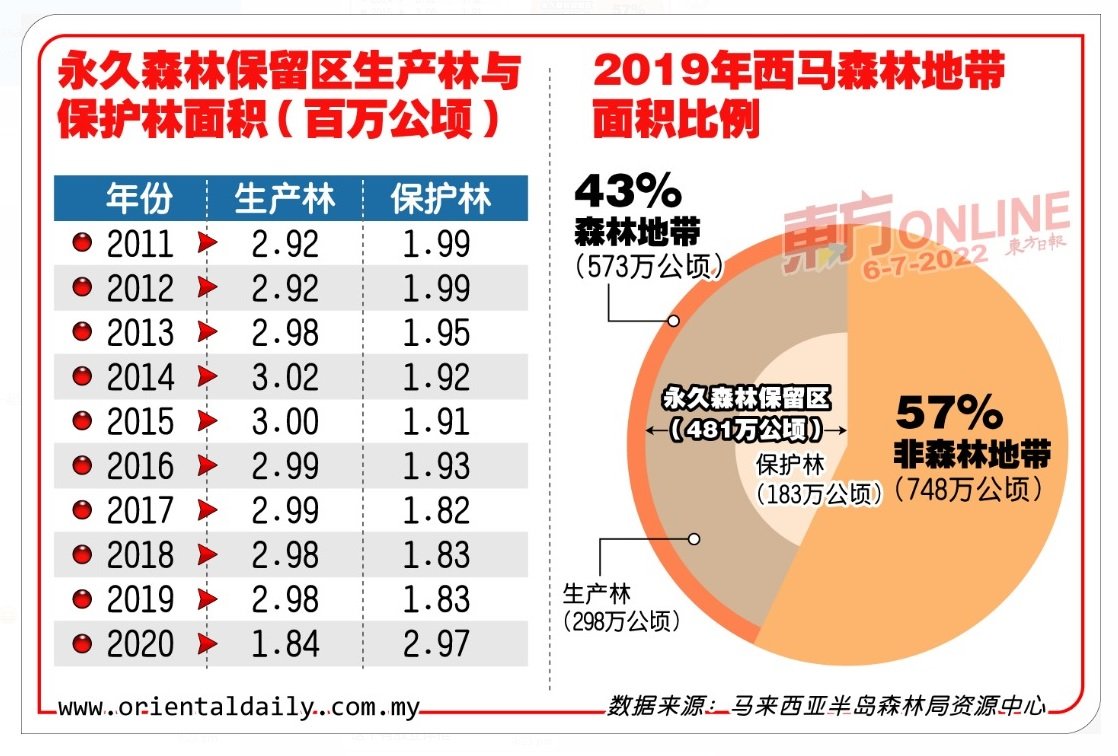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