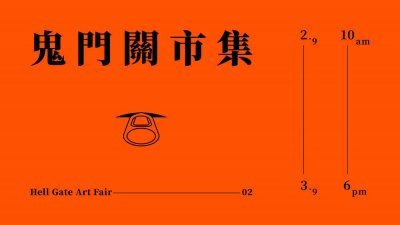办杂志的疯子
全球媒体都在谈转型,纸本行业还能撑多久,根本没人说得准。有人说杂志业已一蹶不振,同一时候,却有另一把声音说新一轮的杂志浪潮正在兴起。无论如何,在数码时代办杂志,尤其是不稀罕商业广告的独立杂志,已被看作“疯子才会做的事”。

很多年前,本地有一本中文电影杂志,第一本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本,叫《电影本事》。然而,创刊3年后,这本让本地电影爱好者著迷不已的杂志因公司重组等因素终究是走向了停刊。无论是搞杂志还是搞电影,都是自讨苦吃的事,可偏偏就是这个人人对纸本是否能持续生存不置可否的时代,本地再次出现独立电影杂志《无本》,背后的推手是一个26岁,目前仍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无本》在面子书上这样介绍自己:“无垠之地,无本之木——冒险的人无惧晃动。”创刊人叶瑞良说“无本”的意思并不是“没有”,反之是“无边无际”,但关于冒险,他直认不讳。这本杂志的横空出世,有影评人感慨幕后班底“是从来没听过的名字”,更多时候是感叹竟有人敢在这种时候办杂志搞出版,年轻人的冲劲被看作一种不知天高地厚。
叶瑞良小名阿良,无论是名字还是外型,看起来都很无害。这本杂志由他个人出资,团队一共5人,平均年龄不超过28岁,而杂志虽叫“无本”,但它的缘起是基于阿良身边刚好有一笔钱。“我工作上拿到一笔花红,不知道要用在哪,最近迷上园艺,一开始打算把钱拿去上相关的课,但后来想想,这笔钱应该用在和电影有关的事上。其实可以拍短片,但我又没什么想说的。于是,就有了不如做一本电影杂志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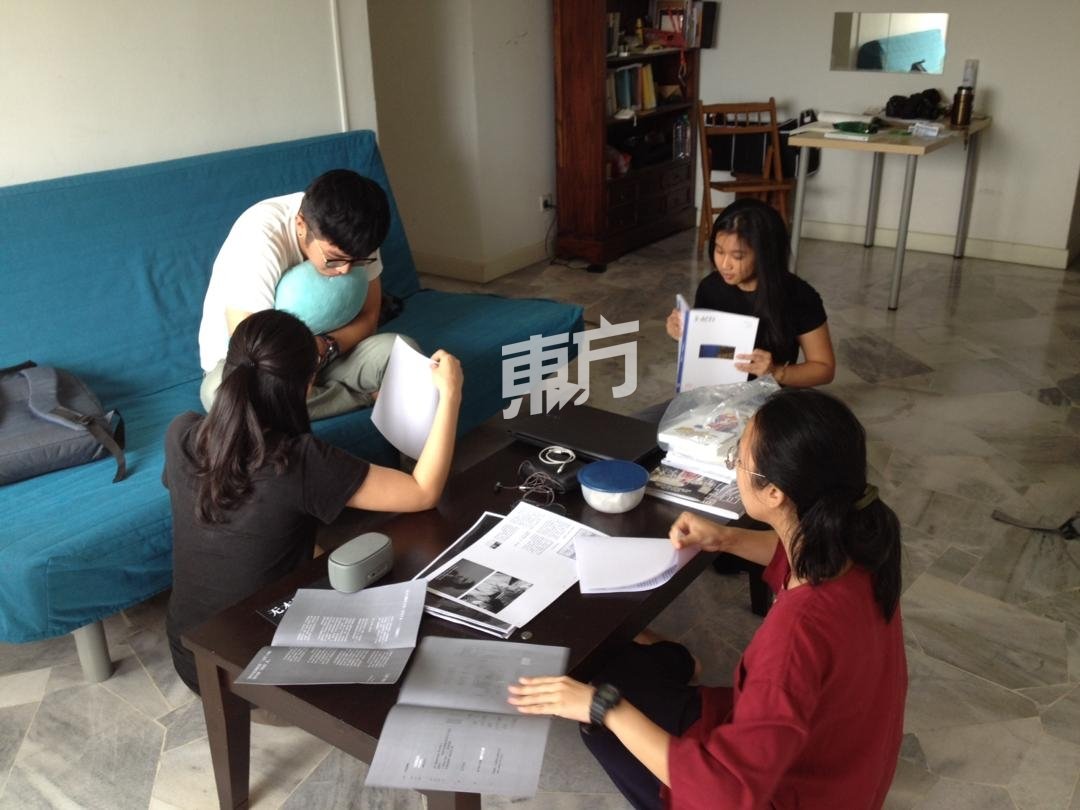
他说自己萌生了念头,却不敢继续往下想,“我觉得要整个团队一起出发,才会有一样的情感。毕竟他们不是帮我工作,我没办法发薪水给他们。”他在编剧工作坊上认识了安角,也就是《无本》的主编,“她现在念著中文系,之前在报馆当专题记者,她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媒体圈朋友,而且对电影很有热忱,我跟她提了办电影杂志的事,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阿良坦言:“我是电影和短片领域的人,对杂志一无所知,手里握著一开始的预算5000令吉,决定就办一本杂志。”他不怕承认,办杂志从来不是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拍长篇电影,至于做杂志,将来回看时,应该就是‘原来我在这个年纪,爱电影爱到这个程度’。”难怪人家说办杂志非常难,因为对阿良来说,爱电影爱到去办一本杂志,等同于一种真爱的表现。
不因资金问题放弃细节
《无本》是季刊,10月出版的第一期印了1000本,耗了1万令吉,比阿良原本的预算多了一倍。“成品的线装设计能让杂志完全摊平欣赏,印刷费增加了30%,页数也从原本的50页增加到100页。有人会说钱是办杂志的阻力,我不否认资金是挑战,但你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问题,就不会再把它当作问题来烦恼。而且,我们始终没有因为钱的问题放弃任何该有的细节。”

任职于大荒电影制作公司,阿良说自己愿意以薪水投资这本杂志,“我想让学生也有能力买,所以价格定在20令吉,但这个价格没办法让我们赚钱,书卖了又有1万令吉可以维持下一期的出版,可我仍是没法给团队付薪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然而更让他在意的是,首期就印了1000本,却不知道要卖给谁,“很多人建议印500本就好,但其实500本和1000本的印刷费差不了多少,我希望更多人看见,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市场,但既然印了,我就会试著把读者给找出来。可能是喜欢电影的人,也可能是喜欢文字的人,为了里面文字而看,也由此认识了电影。”他认为,中文市场确实不大,但不论是电影还是杂志,都需要培养观众/读者。
记录当下 回馈电影圈
阿良毕业自砂拉越大学(UNIMAS)电影系,毕业后就到本地知名独立电影导演陈翠梅的制作公司工作,他认为:“我总觉得我们拍电影是在利用电影,透过影片来表达自我,所以搞一本电影杂志,某程度上是我想回馈点什么给电影圈。”他接著指:“大马电影圈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资讯我们不知道要上哪里找,即使有,大多也是回忆录,可我想记录当下正发生的事。比方说第一期我们访陈胜吉,现在访和10年后访肯定会有所不同。”

之所以是季刊,一方面是让主编有更多时间搜集资料,另一方面是想让自己有多一点时间存钱,“如果能半年出一本,我就能存更多钱,但世界的脚步太快,电影一部紧接著一部推出,我不想错过任何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东西,尤其电影的生命周期非常短,下映之后就难有机会再看到相关的资讯,媒体一般不会去报导旧闻。”他说:“现在我们能应付的是3到4个月推出一本,但我希望将来能越出越快。”
《无本》除了电影相关人物的专访,也邀写手写电影人、谈电影,“无边无际其实未必是没有边际,可能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访美术指导、访幕后工作人员,电影人通常因为电影暂时地生活在一起,拍完了又各自往其它的场域去,我们想把他们从无边无际里凝聚在一块儿,借由文字和影像封印在纸张里。”
创刊后续探索磨合
《无本》第一期已面市,但阿良坦言,在很多方面,团队仍在摸索和磨合中,虽是创刊人也是出资人,但问他这本杂志是否有自己的影子,是不是就是他想要的东西时,他笑说:“其实不是。”他解释:“我和主编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想法,但每当意见不和,我就尝试以我看电影的角度去理解她对文字的态度。比方说,我希望这本杂志是浅白易懂的,但主编认为不可以宠坏读者,若读者只懂ABC那就只给他们ABC,他们不会进步。我一开始不能理解,但后来我意识到独立电影也是这样,不会刻意地去迎合观众。”他对电影执著而主编安角对文字执著,只要认清并体谅这一点,两人就能沟通,就能彼此理解。
价格、媒介语甚至是纸本抑或电子版,团队都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中文市场小,要做的话就要做英文版,但我想做一本自己看得懂的杂志,未来可能会做双语,还有很多的可能性。至于纸本,我始终觉得实体书有它特有的温度,纸张会皱、会氾黄,这些都是它独特的地方,在数码时代做纸张印刷是一种浪费吗?我觉得只要这些纸去到对的人手上,就不会是浪费。”
有句话不是说“要害死一个人,就叫他去办杂志”,正筹备明年1月开拍长片的阿良跨界搞杂志,虽也有想要跪地求销售的不安与焦虑,但更多时候,他是乐观的:“人来来去去,但肯定一直会有人。电影系学生一批又一批,学生出来后也会有所生产,再加上这个年代,有很多人喜欢拍摄。”他说的是读者,也是杂志的幕后团队,“或许有人买了两期杂志就不欲再支持,也或许团队里有人无法坚持下去,但这个领域会一直有人在接棒,生生不息。”

团队里的核心人物都有正职,阿良指,每个人每天无偿地抽出30到40%的时间搞杂志,“听起来很少,但那不是每个月30到40%,而是每天。”现时,资金只能用在刀口上,除了无可避免的印刷费,写手的稿费、采访吃喝和路程的津贴也不可免。
创刊号面市后,收到不少回馈,阿良指:“有读者圈出错字,有的觉得文字太艰深、排版不舒服等,我们以很开放的态度去接受批评的声音,也承认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阿良透露,创刊号目前已卖出一半,但他有感,销量已达顶峰。“翠梅姐带了一些去台湾,12月在厦门和金门有影展,我们也会带过去卖。”目前,有多个网络平台、咖啡馆和图书馆可买到《无本》,也可直接透过面子书专页订购,阿良会亲自将杂志包装寄出。
面子书:无本Wu 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