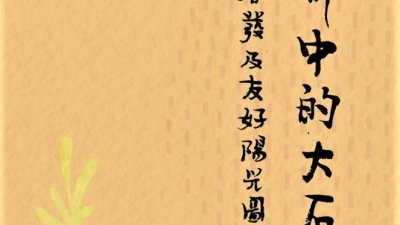猪,是穆斯林忌讳的一种动物,也是让穆斯林敏感的字眼,在国会挑起猪的不当话题被逐出议会厅已非新鲜事。猪在马来文唤作babi,一名马来报编辑告知,马来人觉得这个字眼很粗野,2000年代起普遍把babi改称khinzir,这是源自阿拉伯文对猪比较文雅的称呼。
然而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来半岛也有以babi为地名,在登嘉楼和柔佛便各有一个Pulau Babi(猪岛之意)。20年前笔者因公到登嘉楼,听闻有一个地名奇特的“猪岛”,便与同伴开车沿著登嘉楼河寻访。原来,Pulau Babi并非一个岛,而是登嘉楼河的一个小码头,2002年学者陈志明博士记述,Pulau Babi是登嘉楼华民首个重要聚居地,第一批华民聚居在离登嘉楼河口不远的此地。当时华民在这里种植甘蜜与胡椒,后来衍生出登嘉楼的土生华人(Cina Peranakan)。1967年黄尧《马星华人志》也记述,Pulau Babi与同在登嘉楼河畔的Tirok,可说是登嘉楼华民的发源地。
Pulau Babi地名由来相当逗趣,当年安南人(Annamese)即现今的越南人,经常带著大米与猪只来登嘉楼做买卖,有一回安南人的商船在登嘉楼河沉没,当地华民救了一些猪只上岸饲养,马来人便把当地唤作Pulau Babi。资深文史工作者刘崇汉则称,19世纪末有华民从海南乘船运载猪只到瓜登(Kuala Terengganu),把猪只运到瓜登时就下卸在登嘉楼河中的沙洲或“岛”上暂时豢养,久而久之马来人就把该沙洲称为 “猪岛”(Pulau Babi)。
学者陈耀泉博士有此一说,早年每逢年底东北季候风,就有海南岛和安南的商船在瓜登唐人坡(Kampung Cina)经商,海南人和安南人都卖猪,由于猪只难以分辨,经常引起一些纠纷,海南人为免麻烦便把猪尾巴切掉,那时唐人坡流行这样一句闽南话:hainam tu bo boey(海南猪没尾)。陈耀泉认为,应该是海南猪的肉质比较好,所以才切猪尾巴来和安南猪区别。
然而,华民却不把Pulau Babi唤作“猪岛”,也不直译为“浮罗巴比”,反而称作“蔗铺”,闽南话chia-por,蔗糖铺或蔗糖市集之意。依此推论,华民放弃种植甘蜜与胡椒后,一度曾在此种植甘蔗制糖。陈志明提到,在瓜登崛起成为大埠之前,Pulau Babi是本区域(瓜登地区)的中心或闽南话所谓的phou(埠)。有说早年此地住有数百户华民,兴许如此Pulau Babi也曾被称作“蔗埠”或Cepoh?
反而,离Pulau Babi不远的另一个早期华民聚落 Tirok,至今仍被华民唤作“猪莪”,这可能是马来半岛唯一带有“猪”的中文地名。黄尧提及登嘉楼河畔犹保留三个华民村落,除了“猪莪”,也包括华民对Pulau Babi称呼的“蔗铺”,又包括Pulau Babi直译的“浮罗峇咪”,后两者其实就是同一个村落,有可能称谓不同夹缠失误了。对于“猪莪”一名,黄尧有此一说,“峇咪”就是马来文里的猪,“莪”则是栅栏之意,马来人以此来与华民作为分别。

一般学者、研究者,多把Pulau Babi、猪莪视为登嘉楼华民最早的落脚点,甚至直指登嘉楼唐人坡的华民,也是后来从Pulau Babi、猪莪移民过去。此说多根据猪莪的广泽尊王庙,有一口锺注明乾隆二十七年,也即1762年。问题是,Pulau Babi离登嘉楼河口约14公里,猪莪离河口则为17公里,何以华民不选择落脚河口的瓜登唐人坡,反而转向内陆的登嘉楼河畔发展?
陈耀泉直接指出,坐落登嘉楼河口的唐人坡才是华民最早落脚处。2012年陈耀泉书写猪莪的马来文专书里,引述1719年到访瓜登的英国商贾Alexander Hamilton称,这个港口城镇约莫有一千间房屋,其中超过一半为华民。换言之,即便华民1762年已聚居猪莪与Pulau Babi,但更早之前华民显已落足瓜登的唐人坡矣。
1964年学者Peter Gosling绘制登嘉楼华裔移民地图,显示南来华民先驱1840年移居到Pulau Babi,1890年另一批则移居到猪莪。Gosling之说极其独特,瓜登与马江(Marang)的华民皆在18世纪中来到马来半岛东岸,他们虽然都说福建话及自称福建人,其实他们的老家原在广东省南部、海南岛对面的Liu Chou(雷州?)与Kao Chou(高州?),广东南部海岸的人口基本是混合的,除了粤语方言群,还有海南方言群与客家方言群等,登嘉楼的华民可能先由福建迁移到Liu Chou与Kao Chou,后来再移民来马来亚。“还有一个可能,这些华裔移民不是福建人,而是融入福建/峇峇社群被同化的海南人,一来海南话与福建话相近,二来海南人看似不抗拒被其他方言群同化。”

柔佛Pulau Babi又是另外不同的故事了。原来,在丰盛港(Mersing)岸外有三个Pulau Babi,最大那个叫Pulau Babi Besar,从丰盛港乘船到此约半个小时,另外两个为Pulau Babi Tengah与Pulau Babi Hujung,若是意译即为大猪岛、中猪岛与末猪岛。然而,1924年英殖民官员J.V. Cowgill胪列的柔佛中文地名表,把这个Pulau Babi记述为直译的“布罗马尾”以及意译的“猪山”,1938年张礼千《英属马来亚地理》则记之“峇皮岛”。
说是大岛,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不能与刁曼岛(Pulau Tioman)相比,惟岛上也有七八个小小渔村,住著约100户马来渔民家庭。当地流传一则美丽的传说,昔日有一名渔民的妻子怀孕,她渴望吃当地盛产的海藻,岂料吃了之后竟变成人鱼,伤心欲绝的丈夫也跟著吃海藻同变成人鱼,至今仍有人撞见这对人鱼围绕在大岛吃海藻,甚至在大岛岩石上留下人鱼的啃痕云云。
耐人寻味的是,明明是猪岛何以唤作“猪山”?有人称岛的形状与猪相似,但根据岛上渔民,原来1950年代有一群山猪(野猪)游到岛上,后来不断繁殖越来越多数量惊人,岛上渔民唯有请来华民猎手打山猪,也有说政府派出军人射杀山猪,而残存的山猪最终也游泳迁移了,不过据称岛上仍有山猪出没,但已为数不多。
登嘉楼的Pulau Babi,直至1930年代仍有华民养猪,到后来华民外移也就绝迹了,1970年代Pulau Babi被易名为Kampung Pembangunan(发展村之意),再后来1980年代又改名为Kampung Pulau Bahagia(幸福岛村之意)至今。同样的,当柔佛Pulau Babi的山猪慢慢不见, 这个岛名里的Babi也跟著消失了。2018年10月,时为柔佛王子的Tunku Ismail Idris,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载了两张海岛的风景照片,并指这是Pulau Babi Besar,“普遍被称为Pulau Besar,因为一些马来人对猪的字眼感到恐惧。”
话说回来,Pulau Babi地名并不止于这两个,在森美兰波德申岸外便有个无人小岛叫Pulau Babi,在雪兰莪巴生岸外、吉胆岛(Pulau Ketam)北面亦有一个无人岛唤Pulau Babi,还有在砂拉越诗巫(Sibu)邱炳农路也有一个Pulau Babi码头。在槟城菩提小学邻近则有Sungai Babi(猪河之意),在彭亨文打(Benta)又有个Kampung Babi(猪村),而印尼、文莱也都有Kampung Babi。兴许,一个带猪字的地名无需过敏?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jpg/03a2b382bd08710eeae65bbaef23d1a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