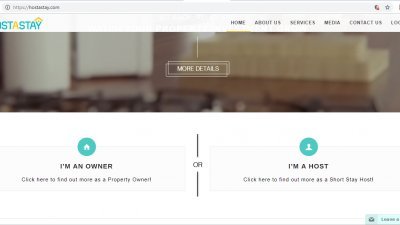大马人也许不熟悉周东彦(37岁),但是他的名字在台湾表演艺术圈中响亮了10年。他是剧场与影像导演,有“影像诗人”的美誉。几年前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亲自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参与最新作品《关于岛屿》的影像创作与设计,他与林怀民花了3年时间一起完成作品,他说:“最困难的部分是让文字像落石一般砸死人。”
这趟是周东彦第一次来马,马不停蹄的行程,让他没有时间好好逛一下吉隆坡,他说这些年到处飞到不同城市工作,早已经习惯了这样工作节奏。话虽如此,这几年他的创作时间拉很长,好像与林怀民合作的《关于岛屿》,以及同时进行的丹麦跨国制作的剧场作品《光年纪事:台北-哥本哈根》,一共花了3年做影像设计,这对于一个创作人而言是十分奢侈的。他点点头,可是想起了创作是一个思考、消化、再吐纳的过程,又补说:“对一个创作来说,3年时间不多不少。”

《关于岛屿》是林怀民退休前的最后编舞作品,即将在今年3月于吉隆坡国家文化宫公演出。在林怀民找上门之前,周东彦就凭作品《空的记忆》在2013年世界剧场设计大展中夺得“最佳互动与新媒体”大奖。
他说,那几年他与团队花了很多时间摸索了即时摄影、环景摄影、4D浮空投影等多媒体影像技术,可是到了林怀民的面前,他都不要这些东西,“他要做印刷体,想做文字。”
当时他对林怀民说,“文字”在流行音乐圈、娱乐圈已经常常被用到,不如别碰好了?“林老师只说不担心,我们试试看吧。”他带了超强团队跟林怀民一起工作,“他们当中有很会做3D建模、打光的,可以把字打得很立体、旋转跳跃的,可是老师都不要这些,他说是噱头,他只要黑与白,不要光影、不要立体。”
3年酝酿文字天灾
周东彦说,在与多媒体结合的很多作品中,某程度上《关于岛屿》是素朴简单、清冷的,“老师很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次他要表现的是文字是什么、语言是什么?现代人对文字和故事的感觉,可能已经渐渐淡忘了,大家只看手机和视频,已经不看报纸、不阅读了。”

林怀民让他们去上课,理解印刷体是怎么来的,那是怎样的官方文字,同时丢了很多台湾文学作品给他们看。“我们开始读字,让它从有意义,变得无意义,再变成图像,字到最后要像落石一般可以杀人,他要呈现一个天灾。4年前,我们听得茫茫然然,然后开始试著做一些东西。”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让诗词慢慢消失,从有意义的诗句,变成一个一个的字词,最后变成河流。老师丢给我们非常多的文学之外,还给我们山名、鸟名、树名,他问我们知道哪些地方,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他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当这些东西开始没有要那么看到其中的意思了,这些在上面流动的字,全都是台湾的鸟类和河川的名字,地名慢慢跑进来了。”他说,最困难的部分是让文字砸死人,“文字像落石砸下,发生大地震,所有的舞者倒地,一片黑暗之中,是文字打造的星空。然后好多好多的词再度浮现的时候,他们会慢慢地碎掉,甚至被海浪冲走。”
演出前两个月,他终于看到团队努力做的影像配合著舞者是什么样子。“突然间我理解了这一切安排的意义是什么。当那些落石落下来的时候,影像组的大家鸡皮疙瘩掉满地,问大家你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说很怪,我说哪里怪?大家迟疑了半天,有人觉得影像终于活过来了。他看到那些文字真的把舞者砸死了。”

林怀民教会我如何生活
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影像的意义是什么?一定要用酷炫的影像才能说故事吗?如果影像在剧场作品中只是一个华丽的点缀,真的有必要耗费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与精力来做这件事吗?周东彦也常常问自己,如何让影像不只是背景,而是一个独特的说故事的工具。以《关于岛屿》为例子,如果拿掉影像,这个作品就不成立了。他说:“部分的演唱会或娱乐节目,其实少了影像还是可以完整听到这首歌的意境,但是基本上影像在《关于岛屿》里不只是文本和脉络,甚至可以是另外一个舞者,我们希望影像在剧场或表演里面,担任的是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装饰。”
林怀民带给他什么影响?他说现在还说不清楚,因为他自己也还在改变。“除了跟林老师学习规划空间,他的所思所感以及速度之外,还有就是学习如何生活,以及待人处事。他会问你有没有看巴索里尼、费里尼的电影,有没有看这个看那个,但他也会问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甄环传》,他活得非常入世。他每天读新闻、读书,也可以很亲切地跟我们聊韩剧、偶像剧,他并不是活在象牙塔里。”

试试做做看,自有新发现
“我其实一直在做自己不会的事”、“我们试试看”是周东彦常挂嘴边的话。他2018年的“一席”讲台上说:“我发现迷路是我一直想办法做的”。绝大部分的人都害怕迷路,而他的路就是迷路。他开始艺术创作,是因为对人生有很多疑惑。“我不介意迷路,尤其是以前,可是最近比较…”他顿了顿说,“现在我正在经历那个‘Lost’的感觉比以前更强烈。”
迷路,可以指很多事情。37岁的迷路,是此刻创作与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我成立了一间制作公司,但是我们都在做很不商业的纪录片,虽然是一间公司,但并不是非常赚钱,仅仅够应付我自己和公司的日常运作。”他继续说:“我心里一直想做创作,而且相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拥有一些资源和机会,可是以前刚毕业的时候拿到15万台币(约2万令吉),之后拿到100万(约13.3万令吉)的机会,到现在拿到300万(约40万令吉),可是钱永远都不够,并不能养活自己;然后从25岁到37岁的我,我的父母也老了10岁。”他说艺术家对于生活的焦虑,与普通人没有差别。
创作上的迷路,周东彦不一定不知道方向,而迷路是一个学习选择的过程。他在创作上一直抱著走走看看的心态,尝试挖掘不同的可能性,“人生难免会有搭错车的时候,不得已到了一个地方,不妨坐下来吃个东西或什么的,可能会比跟著旅游书更有趣。我们永远都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当然你也可能遇到不好的事。”

“我们都被标签是年轻世代,但是我现在并不是非常适应IG的语言,我懂这些科技,可是不觉得自己操作得非常好,更别提抖音了吧。”他不是怕自己跟不上,而是如何找到年轻人的语言,与他们连结。“我之前拍了很多纪录片或艺术影音,我知道这些作品很有趣,也绝对有它的观众群,可是新的一代更享受刷手机里的世界,多于看现场表演,我想这个焦虑是全人类共有的、有感的。”
他笑说,从事艺术的人可能都想很多,情感很丰富,“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忧国忧民,回到艺文创作者的身份,我到底要说甚么?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的作品在现在还跟我们有关,实在太伟大了。然后呢?它现在跟15岁、18岁的人要怎么样有关。好比很多芭蕾舞者在IG上非常红,他们已经红到更在乎那个瞬间的照片多过他们在台上的表演了。
因为没有人看到他在台上拼搏了两个小时,大家只会看到他在IG上的followers,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世代,值得我们去思考。”如何呼应它,如何跟它相处,他保持谦卑,“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答案。”那就继续试试看、做做看吧,自会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