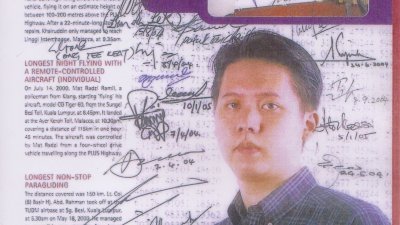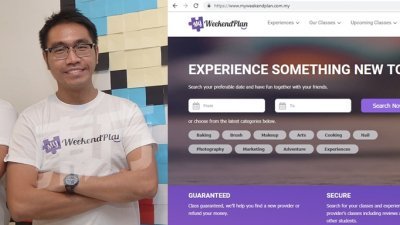2016年廖克发完成他的首部纪录长片《不即不离》,但因内容触及马共课题,被大马电检局列为禁片,他因此开放线上免费放映,7天内吸引10万人观影,在本地引起不小的话题。本科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系,当过小学老师,廖克发说他没有电影梦,拍纪录片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所缺失,想要把那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给找到。
新加坡国大毕业后,廖克发在当地任职小学老师,待了四五年后,27岁那年,选择到台湾国立艺术大学修读电影系,“我去台湾念书是因为那里相对自由,我想去感受新加坡所没有的大学生活。我主修金融和市场,大家只想著如何赚钱,不会去想谋生以外的其他事。”他说:“惭愧地说,我当时申请就读的其实是电影硕士班,我去面试,他们问我有没有作品,我说没有;问我是不是因为侯孝贤而来,我说不是。”知名导演侯孝贤是台艺大前身国立艺专毕业生,如今是台艺大名誉文学博士。
后来,校方要求廖克发先取得电影的本科学位,他心想“没关系,反正只是想体验大学生活”,也就接受了。“我靠著之前的存款上大学,大二下半年时,积蓄花得差不多了,这书是念不完了,就把剩下的钱用来拍摄短片《爱在森林边境》,拍完后,没上大三,就回新加坡电影制作公司工作。”他坦言,辍学是因为大学生活已经体验够了,虽说那时已经爱上了电影。

短片获奖 决定未来方向
《爱在森林边境》是廖克发的第二部片子,第一部短片是大二时描写女性情感,关于堕胎课题的《鼠》。这部片在2010年一举夺得台湾金穗奖优等学生作品奖和最佳导演奖,也决定了他未来的走向。他忆述“《鼠》得奖时,我在新加坡工作,某天深夜,接到台艺大指导老师吴秀菁的电话,她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打工啊,在拍减肥节目。她骂了我一顿,说没多少人大二就能拿到资金拍片,如今还获奖受肯定,她说我应该珍惜这样的命运。”于是,他领了奖金后,回到台艺大完成了学业。
2017年2月向廖克发约访时,他希望能以宣传片子为主,表明不想接受个人宣传,所以统一拒绝个访。一年多后再次提出邀约,终于与返马参与自由电影节(Freedom Film Festival)的他见面。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抗拒个人专访,只是大部分时候希望人们关注影片大于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然而,矛盾的是,纪录片常常投射创作者的情感。他说:“拍纪录片的人就是让被拍的角色面对心里的怪兽、心里真正害怕的东西。我拍《不即不离》时,怕的是父亲,害怕去整理疏离的关系,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逃跑,试图离得远一点。”
追溯过去 容纳真相的细碎复杂
《不即不离》对廖克发而言,是相对重要的一部片子,他试图追溯原生家庭的历史,为了了解曾是马共成员的已故祖父,不得不“试图靠近”父亲,主动向他提问。
“拍的时候我从没想过这部片会被禁,它以家庭为出发,谈的是很Common(普遍、共有)的问题和课题。”他坦言:“我觉得自己有所缺失,有很多‘为什么’需要被解答,包括当初我因为不喜欢马来语而选择念独中,但原来在我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上本地大学的机会。我心里是很郁闷的,为什么条件如此受限,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因为拍这部片,我逐一地去回看这些过去,为它们找答案。”
一般认为,纪录片必须是真实的,被看作历史的记录。廖克发直言:“其实很难为纪录片下定义。纪录片必须要吸引人、能打动人,但它不一定是‘正确’的,拍片的人不是法官,他只是制造了氛围和情绪,让你自己去思考。”他认为,我们念书时读的历史是平面的、线性发展的,我们对那些人事物不抱任何情感,“真相本来就是细碎复杂的,我们必须容忍它是这样的,因为那就是真实的一部分,对也好,错也好,要采纳这个说法还是另一个,拥有都接受的胸怀才是真正的多元。”

偏见和歧视无可避免
然而他也不讳言:“其实我觉得没有所谓的‘真实’,人都是以偏概全、歧视和主观的生物,所以纪录片也许有偏见,也许是持怀疑态度的,你甚至会感觉到他在说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掩饰心里的矛盾,但人的可爱也正是出自偏见和歧视,爱情就是偏见的一种,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也无需理由。”
换个说法,通常被官方采纳的历史只有一种,但是不是其他的说法就该被否定?廖克发坦承:“我拍摄《不即不离》时,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历史和记忆,哪个比较重要?几乎每个组织都有个历史,但历史说法总是比小人物的集体记忆来得重要,为什么个人的记忆会不重要呢?他说的和她说的,是这些拼凑出过往,记忆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个说法,就代表另一个人说的没发生过。”
身份持续变动 不想活在简单分类中
在台湾生活了11年,娶了台湾籍太太,廖克发特别不喜欢去区分和讨论大马和台湾的差异,“用国家来划分人是很危险的概念,是过于简化的方法。”独立电影被标签为成本少、看不懂和内容沉闷,但廖克发反问:“真的是这样吗?”他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是二战后,电影人走上街头去拍摄纪实、关注社会的片子,而台湾的新浪潮是创作者在思考“台湾人是什么?”,“这样才叫‘独立’,事实上当年我们的‘Merdeka’指的独立也不是国家的独立,而是人的独立。”
关于身份,他说自己一直在找,而且几乎不会有终点,“身份是变动的,在台湾,他们说我争当地的资源拍大马的电影,在大马,人们又说我怎么在台湾发展。”廖克发接著指:“19世纪初,如果问‘你是什么人’,得到的答案是福建人、客家人、广东人,后来变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身份一直是别人赋予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潮流,但你想要活在这种分类里吗?只有利益当前时,才会把人分类,我觉得不应该把东西太简化。”
同样的说法,用在纪录片导演这个称号上,也一样适用,“定不定型是别人的事,要如何把我分类,我没关系,毕竟分类是为了方便。”他透露,接下来还会拍好几部关于大马的影片。创作者都想获得认同,廖克发分享,曾有前辈说,现在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上,最多影展的时候,但也是最少电影可以留存下来,更长久留在观众心里的时候。他回想起2008年拍毕《鼠》,把它拷贝在光碟里带回来给家人看,但他们都说看不懂,“所以我把它了收起来,心想‘算了’,但某天半夜,母亲把它拿出来再看一次,她或许是想了解这个儿子,又或者她真的很想看懂这部片子,但无论如何,这件事影响了我接下来拍的片子。”
他认为,市面上有太多典型的纪录片,于是人们对影像的敏感度不高,也懒惰思考,“他们要你直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的专注力变得很短,体验事情的能力退化,容易被操纵。在社交网站上,决定要不要按赞的时间就那么几秒,建立在冲动上,很多时候,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感觉。”《不即不离》累积10万人观赏,有赞也有弹,“我都试著去听。但片子到最后是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创作者其实也不真的会去迎合任何人。”他补充:“片子的寿命其实也不真的局限于完成后的那几年,真正的挑战在10年后,会不会还有人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