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刘嘉美
婆罗洲有著世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之地,但难敌数十年来无休止的砍伐与开发。目前,砂拉越原始森林数量仅剩下5%,辽阔的古老雨林只余下最后一片未被污染的绿地。守护这片森林的,正是在深居于森林深处的本南族(Penan),他们世代以路障抵挡伐木商进入,抵抗已成日常,族人也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在开发计划下,本南人如何守住这片原始森林,又面对哪些生活困境?
我随著非政府组织“当今峇南”来到位于峇南河上游的本南族人聚居地。“当今峇南”于2013年成立之时,正是峇南水坝计划正准备启动的时候。
自2013年起,峇南一带的原住民为了保护家园,自发组织起来,在主要的工程出入口处,设立路障,驻守超逾两年,不让工程人员进入,最终成功挡下水坝发展计划,政府宣布正式取消兴建水坝,两万名原住民得以保住家园,389平方公里的森林不至被淹没覆盖。
在更为内陆的峇南河上游地区,接近印尼边境的色仑戈(Selungo)一带是本南人的居住地。本南族是众多原住民族群中,人口少、居住在更内陆之地、更为与世无争的族群。我们到访的两个本南村落弄沙益(Long Sait)与弄克隆(Long Kerong)皆没有道路可进,只能依靠小艇与步行。从砂拉越的美里出发,经过7小时车程,转乘3小时小艇,再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设路障阻挡伐木
在砂拉越内陆地区,所有道路几乎全由伐木集团出资建造。集团建路的目的,是为了能进村伐木。有了路,大型机器与重型货车便能开进森林里,砍伐与运送木头。伐木公司运出来的不只是雨林里珍贵的木头,还有廉价的劳动力。
多年来的砍伐使环境严重破坏,原住民难再以森林为居,水源污染、动物绝迹,先祖留下的森林已不复再,传统的生活方式无以为继,青壮年的原住民只能往城市去,从事比城市基层更低薪的工作。
但是,这两个本南村落和其他的原住民村不一样,伐木路并无开设在他们的地方。弄沙益的前任村长比朗(Bilonguyoi)说:“伐木公司一直想进来我们的森林砍木,我们的村民会设路障阻挡,不让他们进来。”
村民一直不让伐木商进村,伐木商无法砍伐树林,也就不在此地建路,因此,路途遥远、与世隔绝,不全然是地理位置所致,更多是人为抗争的结果。
起诉伐木公司 村长卧尸河边
相对于资源分配上的歧视,有时抗争的打压来得更激烈。同样位于峇南河上游,就在弄沙益村附近的弄克隆村,前村长柯里绍(Kelesau Naan)长期组织村民,阻挡伐木集团进森林伐木,又以自己的名义入禀法庭起诉伐木公司,以维护村民的土地权益。
2007年10月23日,柯里绍离家到森林检查捕猎的陷阱后,再也没有回来。两个月后村民才在河边发现他的尸体,死因不详。
出事之前,村民与伐木公司的关系特别紧张。布鲁诺曼瑟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卢卡斯斯特奥曼在《黄金伐木》一书中记载,同年4月,伐木集团曾派出保安人员,拆毁村民设置的路障,其后在6月份柯里绍被伐木公司的人员恐吓。于是他与邻村村长比朗合写了一封投诉信。 +
为了能进森林伐木,伐木公司还多次派人游说柯里绍,提出只要他放弃抗争便会为他和村民提供经济协助。但这位村长一如既往,断言拒绝公司开出的条件。而在他出事后的两星期,曾有神秘探访者乘坐直升机到达村里。主动无条件给予村民3万令吉作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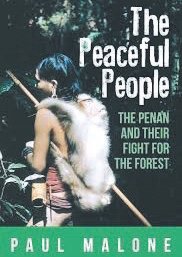
事发后,警方始终未有派人到发现尸体的现场进行调查,即使布鲁诺基金会在国际上把事件曝光,警方最终仍以“自然死亡”来总结柯里绍的身亡。
柯里绍的家人和村民怀疑前村长是被杀害的。柯里绍村长离世后,清迈和马来西亚等人权组织,分别在2007、2008年追颁人权奖予他本人和组织。我们走在本南人守下来的原始森林中,这里不曾有推土车、伐木机驶进来。我们走在茂密的丛林中,村长约翰细细介绍各种已难在其他的砂拉越森林发现的珍贵树木和植物,像砂拉越的铁木(Belian)。
他温柔地轻拍著粗大的树干说,“这树是不会死的”。
本南人会按树的生长情况、位置,把树破开分二,其中一边便会长成新树,生生不息,延续著原来的生命。柯里绍,以及更多因为保护雨林而牺牲的人或已不在,但他们的抗争精神如铁木般留下来,继续鼓励著内陆里的原住民。权利并非从天而降,有些事情值得不惜一切来捍卫。柯里绍生前说过:“如果没有我们的路障,这片美丽的森林很早就全被砍掉了。”
本南人守护的森林,不为个人,而是为世界而守。
2660个足球场面积 树林一年内消失
在1967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建议,砂拉越森林每年的树木砍伐量应以440万立方米为上限,以维持森林生态的可持续性。当时,砂拉越的砍伐量大致在每年230万立方米,未超出建议标准。但1981年以后,情况便急转直下,从砍伐880万立方米,到隔年砍伐1100万立方米 + ,再发展到高峰期的1940万立方米,相当于2660个足球场大小的树林,一年内在砂州消失。
近年砂拉越的树林砍伐量稍有回落,维持在每年800万立方米左右,并不是因为情况有所改善,而是可砍伐的树木所剩无几。
时任砂州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在2013年的一次电视访问中,否认森林消失的问题,“砂拉越的森林仍然丰沛如昔,这可以从“谷歌”的卫星图片中看到,砂拉越有84%的土地仍然是森林地” + 。但是,国际非政府组织随后指出,这84%的“森林地”包含了油棕园,有自然作物覆盖的土地只有65%,而没有经历砍伐等人为破坏、仍然维持原生态的原始森林只剩下5%。
对于砍伐的看法,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有不同的看法。澳洲记者彼得马龙(PaulMalone)在他的著作《和平的人:本南族与他们的森林抗争》中,如此描述:“伊班族、加央族、肯雅族等原住民,面对伐木公司入侵他们的土地和河流,通常都较愿意接受赔偿;而本南人则更常以和平抗争来反对伐木。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分别是,本南人不要赔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伐木。”
有的原住民认为可以接受有限度的砍伐,但交换条件是为原住民提供学校、诊所、道路设施和赔偿;本南族人希望森林能保存原来的生态,就像他们的祖先留给他们的森林一样原好无缺。

对森林取之有道
弄沙益前村长比朗认为,森林不能被砍伐,“因为森林对我们本南人、甚至对整个世界来说是有益的。”本南人相信万物有灵,对森林充满敬意,他们传统上是游牧民族,相信自己只是地上短暂的过客,理应减少对森林的打扰,不应干扰原来的和平与平衡。
本南原住民谈到对伐木的砍伐,没有深奥的理论,但足以颠覆现代社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树木既不是你们做出来的,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把她砍掉!当推土机把土地撕开时,你会看见她的血液与骨头,她甚至会说话,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土地在哭喊:我不想被杀!”
对森林,他们取之有道,打猎杀生不为享乐,只求裹腹。要是在森林里,看到动物母子,他们只猎取老的,小的会带回家当作宠物收养,直至老死。打猎所得,村民会互相平享,即使是猎人自己,也不会取最大的份。因此,本南语言里没有“谢谢”,因为共享本是必然,谢谢也就变得多余了。

抗争代价:基建严重落后
本南族人原本与世无争,抵抗只是无可选择的防守,弄沙益前村长比朗说:“做路障阻挡伐木商不是为了破坏式的抵抗,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谈判。我们不擅于用视像录影、也没有电话,路障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让政府看到我们的情况。”
晚上的村落特别宁静,只剩微微的灯光。村长敲响钟声,召集村民参与晚上的对话会。
反水坝运动的原住民领袖菲力(Philip Jou)远道而来,捎来了好消息:砂州政府宣布取消峇南水坝计划,村民们都感欣喜。他们没有因为村落所在地不是蓄水区,而置身事外,因为“整个森林都是我们的家园”。
村民地位平等,即使夜已深,仍然积极表达他们的问题与期望。
有妇女表示,希望能为村里新建的教堂加添窗帘;有村民说,当地议员数年前答应兴建一条连接另一本南村的行人桥,但迟迟未建;亦有村民反映,明讯电讯公司在村里建了电讯塔,但讯号接收极差。这些问题看似琐碎,但都与村民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基础建设,包括道路、桥梁、水电、通讯系统的严重缺乏,正是本南人抗争的代价。政府进行资源分配是根据人民的服从程度,而非按需求而定。相对于其他内陆村落,这两个本南村的设备还更为落后。

争取村里建中学
这里没有医院,只有一所小学。现任村长约翰(John Uyoi)说起,他小时候,从家里走到学校,是一段充满挑战的路程,“我们要步行两星期才到学校,赶路到晚上,便摘一些树枝,在森林里扎营过夜。从一个社区到一个社区,我们都是靠走路。”路途中间还有河流,遇上下大雨的时候,水位急涨,他们便要临时制作木筏,才能渡过湍湍急流,走到对岸。
然而,最难捱的,还是对家的思念。上课的时间只能寄宿在校,假期才能回家,约翰曾试过逃跑回去,老师校长也来劝他继续学业,“当时我真的太想家了,不想再回学校,所以到现在我们仍然努力争取要在村里建一所中学。”
在本南村的发展上,政府长期缺席,但村民和非政府组织仍然尝试以民间力量,来解这些决日常面对的问题。例如布鲁诺基金会(Bruno Manser Fund),透过筹款和招募义工,成功为弄沙益村建成一条新的吊桥。又,当明讯电讯塔的接收范围有限时,村民们便合作在电讯塔附近,建了一个资讯站,让村民可以在那边轻松地使用网络。这些都是以民间的动力,来回应政府长期的不作为。
全民看数字:
砂拉越没有经历砍伐等人为破坏、仍然维持原生态的原始森林只剩下 5 % 。





.jpeg/21ba3c609dd0925e452aaa1722129051.jpeg)




.jpg/37c4c961c711ea241835a10559300496.jpg)
.jpg/bdb07866a9bdda3bca113d097978dfb1.jpg)





.JPG/6f16eaeafb8220db4316bb12c8e44cee.JPG)




.jpg/c72e9e9935e9f2103a60bf54abd73e1b.jpg)
.jpg/394b4ccdfcc914d1cc84f80d0225fece.jpg)
.jpg/e315a292a446232fd2384d24055c2ac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