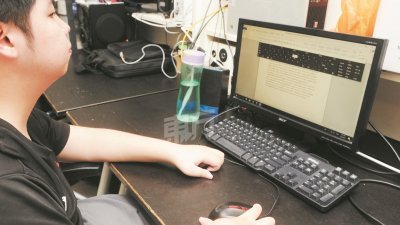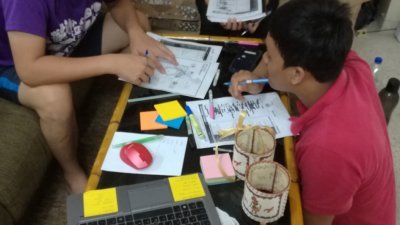移居美国35年,陈介福(Kirby Tan)这三个字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华社是掷地有声的名字,他参与华侨活动,也和美国人打交道,同时以在地大马人的身份协助马来西亚官方推广大马美食,促进贸易出口。每每人们问起何以愿意出钱出力,他都笑称:“因为我是大马人。”想要深究,稍待半晌,也还是同一个答案,直接而纯粹。
即便大半生在海外生活,也不讳言大马人的身份并没有带来多大便利,但陈介福始终记得自己来自美食云集的古城马六甲。2009年年底,由大马政府发起的马来西亚美食厨房计划(MKP)正式授权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负责实行,在全球7个站点推广大马美食,作为活跃于纽约的商人,陈介福出席了会议。

他透露:“当时我还没开餐厅,MKP也还没真正开跑,因为在社区活动里经常负责煮食,刚好2013年时,有一名认识了很久的业主提供诱人的店租,于是便与人合伙在新泽西利堡(Fort Lee)开设了第一家售卖马来西亚美食的餐厅。接著2015年,到纽约开设马来乡厨(Malaysian Kitchen),餐厅的对面就是自由女神像,内外加起来有约180个座位,是当地最大的大马餐厅。”
同时,陈介福也获MATRADE纽约办事处授予进行展销会的合约,代表大马推介多元文化美食。事实上,美食之外,展销会亦是陈介福的专长,从事广告印刷行业的他总是无偿设计和赞助活动需要的印刷品。关于大马的美食,他发自内心地引以为傲,“我们的食物对老外来说很特别,很具新鲜感,他们好奇,展销会时我们推介椰浆饭,周边挤得满满都是人。”他接著说:“海南鸡饭起源于海南岛,印度煎饼来自印度,却是大马把它们发扬光大。”

在饮食文化单一的异地推广大马美食,陈介福懂得动脑筋,“既然是要推广给不认识或不熟悉亚裔饮食的黑人、白人,那就要走进他们的地方,而不是在唐人街搞活动。”马来乡厨设在纽约金融区,陈介福和团队也走入当地人聚居的社区商场进行美食展售,食品搭配亦见巧思,“惹当披萨很受欢迎,还有咖喱意粉、用烧鸭材料腌烤的火鸡等,你光说咖喱他们可能不太能接受,但因为是意粉就比较愿意尝试,要有至少一样他们了解的东西,接受度就会提高。”
马来西亚近年国际形象不佳,但离家生活反而对身份认同有另一种体会,对于种族隔阂这一点,他倒是相当感触,是次特别回马参与马来西亚国际清真食品展(MIHAS)等官方活动,他说:“在大马,我们会说自己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但在美国,我们只说自己是大马人,不会特意强调种族。”
留在国内的人想出国,在国外的人想回家,然而陈介福坦言“回流”的念头已经过去了,“以前有一阵子经常说要回来,毕竟亲戚都在这里,但现在3个女儿都长大了,她们是在美国成长的一代,我们也没太执著一定要哪生活。”

家人在哪,家就在哪
陈介福叔父辈当年南来时落脚香港,他的父亲则去了新加坡,后在马六甲成家立室,对成长于古城的陈介福而言,两处都是乡,“当年911恐袭时,婶婶拨电给我,说美国太危险,让我赶快回来,她的‘回来’指的是回香港,但我飞回马之前先去香港,我妈会说‘不是应该先回家吗?’,她指的‘家’是马来西亚。”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国宝级画家陈介保是陈介福的哥哥。

今年8月就要迈入花甲,陈介福对家并没有实体的概念,更多时候,是一种情怀,“反正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有家人的地方,都是家。”年轻时跑到单程飞行就要耗上逾20小时的国家生活,陈介福不否认美国确实让人怀抱梦想,“虽然我当初没有刻意规划要留下,但那里确实是只要肯做不会饿死,只要肯努力就肯定有机会的地方。那里有法律管制歧视,有最低工资的限制,也有科技上的便利性。”他笑说:“我有个瑞士的客户,30年来没见过面,一切都是文件你来我往地寄发,都用网络在做事。”
当年飘洋过海 只为完成学业
美国华侨约100万人,但当地没有正规的学校教中文,于是家长们就自行创立中文学校与粤语学校,孩子在学期间,陈介福活跃于校内事务,也曾被推举担任校长。事实上,他一直活跃于社区,曾是新泽西州中美商会董事,参与该州爱迪生市狮子会,担任华人协会服务中心董事等,并曾获得新泽西博根郡社区大学颁发出色亚裔领导人奖,也被列入2006-2007“美国名人录”。
陈介福是当地唯一从事广告设计的大马人,他与马来西亚驻纽约领事馆关系良好,无数次协助领事馆举办与马来西亚相关的活动。他指:“基本上大马相关的事务,都是我在办,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华商相当凝聚,周末也不时会和领事馆的人打球,我这边就像一个总站,电话总是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他打趣道:“真的什么都找我,找老公也问我。”在美国多年,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的911恐袭和两年后的美加大停电,“我们有群组,发生大事会互报平安,领事馆则会打电话过来向我追踪。”
作为异客,在别人的地方以自己的根活出了价值,但其实陈介福25岁那年动念飘洋过海只是为了完成学业,并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我中四就辍学了,家里是做广告的,从事一些修图的工作,辍学出来打工存了一笔钱后就开自己的分色公司,那年是1979年。1982年一个人去澳洲,用搭顺风车的方式玩了两个星期,发觉其实人生有很多选择。”1984年,他决定继续未完成的学业,用自己赚来的钱去美国上高中,再读大学,“其实原本想去英国,那个年代,很多朋友都负笈英国,但美国入学比较容易,汇率也比较可负担。”

面对逆境,保持正念
陈介福说起初期在美国生活的细节,主动提到的大多是幸运的事,包括在最初落脚地加州圣地亚哥待了3个月找不到工作,用仅存的99美元(约400令吉)买了机票前往纽约,因为有广告业的背景,很快地就找到了工作,“因为办公室在新泽西,意大利老板买了车让住在纽约的我代步,后来干脆帮我付了买房的头期,让我搬到新泽西。”
在这家公司打工5年后,他开创自己的公司,正式走上经商之路。看似顺遂,他也承认顺遂,但这当中有的是他认为不足为道的苦,“我工作和上课都是选‘全职’,美国的大学可以自己安排时间表,我就安排3天全天上课,4天全天上班。上班的日子,日夜兼差,白天的工钱当作还老板的房贷。”挨穷的日子也不是没有,“买一盒10粒的鸡蛋,再买一盒菜脯,菜脯蛋配白粥,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也不觉得特别惨,忙著念书和工作,日子一天一天过。”
等到生意上了正轨,一切看似无忧时,偏偏又有避不开的坎,真正要提磨难,他说是为离婚和公司打官司时,“顺利的时候,事事都顺,不顺的时候,事事不顺,两起官司几乎同时期,两年内花掉至少250万美元(约1000万令吉),当时觉得损失的不过是金钱,问题能解决就好,但现在回想,确实心痛。”抱著宁可别人负我,我也不愿负人的心态,即使感情和事业皆受创,陈介福仍坚持要摆正心态。
一心扮演好桥梁的角色,为大马在纽约推展的商业活动尽心尽力,他自问从不问回报,“我能提供的不外就是我的专业,是我原本就会做的东西,其实没什么。”是次回国,紧凑行程和众多待办事项里,其中一项是在本地为世界第一台裸眼立体手机Q Phone寻找生产线,陈介福利用他多年累积的人脉和经验,一步一步促成许多看似不容易的事情,但他做人格外低调,此前不曾接受本地中文媒体访问,默默地当一枚螺丝钉,安守本分,功能大却不张扬。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jpg/e3887b503c2314328d2c45bdf5bea0c9.jpg)
.jpg/1f0b0d6144480d319d9508f2185df601.jpg)
.jpg/96253d1cd3f0c9b41414d67116e1be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