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移工经常迁移至较富裕国家,惟在国外,他们被排除移工保障,因此也容易受到他人虐待。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迫使移工权益恶化,但一些移工已找到抵抗的方式。
根据《New Naratif》报导,去年4月,9名越南妇女一同在手机摄像镜头前录影,向其国家政府及当地支持者发出求救信号。视频中,一名妇女戴著眼罩试图掩盖她的伤势,她称这些伤口是她的前雇主造成的。
在录制的视频中,她们解释称自己是被困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间驱逐中心,她们表示需要外界援助借此回到越南。
其中一名妇女H'Tai Ayun表示:“雇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没收我们的物品、护照证件、或工资。”
相关边境因疫情大流行关闭,一些妇女已经在驱逐中心滞留了数月,有些妇女则滞留了超过一年的时间。这些妇女们控诉雇主对她们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拒绝为她们提供医疗保健,并且还让她们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H'Tai Ayun非常急迫地想回家,她恳求她的雇主允许她离开,惟并不获雇主同意,她便连续7天拒绝说话。当雇主将妇女释放给安排她工作的沙地阿拉伯机构后,她开始绝食,并要求将自己送回到驱逐中心与其他妇女见面。她告诉该机构:“如果你不让我回家,我就死在这里。”
H'Tai Ayun向New Naratif媒体记者透露,视频中的其他妇女也曾试图向招募她们的代理人员及越南大使馆拨电,寻求救援回家,但未能成功,因此她们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求助,该视频也被转发分享了超过10万次。
截至去年11月,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船民救援”的组织者看到了这段视频,并立马帮助她们乘上了一架航班,与一队刚比赛结束的越南球队一同返回,因此大多数妇女目前已回到了越南。
另一名移工Lan也希望能乘坐该航班回家,但她没能“找到座位”。“我很难过。每一次有航班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我回家的时间,但到最后却不是这样。”她为期两年的雇佣合同已在2020年10月到期。
即使在疫情前,东亚和中东较富裕国家工作的东南亚移工,也是最缺乏保障的移工阶层之一。他们往往被排除在所在国的移工法之外,也缺乏法律追索权,因此他们容易受到权力被剥夺和虐待。自2020年起,各地为遏制疫情蔓延而实施了行动管制令,及其产生的经济影响,因此也加剧了这些移工们的脆弱性发生。
国际移工联合会组织者表示:“由于这次疫情缘故,住家式的移工工作时间变得更长、工作量更大、没有休息日,获得的个人防护设备的机会也有限,还会面临未支付工资和身体及精神健康上的问题。”
尽管如此,一些来自东南亚的移工还是找到了他们自己的抵抗方式。
抵制歧视
亚太地区有超过3800万名移工,即使不计算中国的2200万移工,亚太地区也比任何地区来得多。大约有420万名移工源自于东南亚,那里的工业化和环境遭到破坏使当地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地区从事低薪的非正式工作,因此难以养家糊口。这些移工大多数是来自菲律宾、印尼和越南的妇女们,她们移民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区,甚至是远至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在香港地区,当地政府已经制定了专门针对移工的疫情相关政策。在去年4月下旬,香港政府挑选了大约37万名外籍移工进行大规模检测和疫苗接种,当中有两人检测呈阳。而其他职业和其雇主则没有被包括在该政府计划中。
一名37岁担任印尼移工工会秘书的印尼籍移工Aluh Ibrahim表示:“这是香港政府对移工实施的歧视行为。”
自去年6月以来,每当Aluh Ibrahim去采购食材时,她都会穿上一件印有红丝带的白色T恤,这是当地一项名为iRED的运动标志,意指“我抵制排斥和歧视”。
iRED是由香港的印尼和菲律宾移工工会共同组织,iRED反对专门针对移工的歧视性防疫政策。
除了穿上iRED衣服,Aluh Ibrahim也参加了与印尼领事馆官员的在线对谈,她请求对方支持移工在香港的强制检测和疫苗接种计划中获得参与。她还参加了一个在线宣传活动,谴责在香港疫情应对措施中,他人对移工的歧视。
Aluh Ibrahim控诉:“每个人都有可能感染病毒,但为什么只有移工被要求接受检测及被迫接种疫苗? 移工被指控是传播病毒的源头,但与香港当地民众相比,感染病毒的移工数量占非常地少。”
她续说:“只要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我们就不会拒绝接受检测或接种疫苗,这应该也要适用于在香港的每一个人。”
在香港,对移工歧视的问题不是从疫情导致开始的,移工的最低工资保障已经低于其他移工。移工每天往往需要工作超过12小时,每月的最低工资为4630港元 (约2500令吉) ,加上雇主提供的膳食或1173港元 (约630令吉) 的食物津贴,每月的总收入约为5800港元 (约3120令吉) 。对于其他工人,法定最低工资定为每小时37.50港元,以每周工作40小时来计算,相当于没月6000港元 (约3230令吉)。
最终,在香港中央政府大楼外的示威活动,以及来自菲律宾和印尼政府的施压下,香港政府与5月4日取消了强制性疫苗接种计划。然而,在第一轮提供样本的34万名移工中,仅3人检测结果呈阳,因此强制检测要求在第二轮中仍然有效。

遭贩卖至摩洛哥
尽管在香港面临著歧视性的政策,但Aluh Ibrahim却享有其他地区移工所没有的自由。例如,香港和台湾的法律允许移工在当地成立工会,而新加坡和沙地阿拉伯则是被禁止的。她能说粤语和英语,所以她能理解她的雇佣合同和当地的法律制度。如果她遭遇虐待,她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拨电话给工会寻求帮助。
一名来自印尼的45岁的移工Setia,于2020年6月从她的村庄出发到摩洛哥工作时,身上没有雇佣合同,也没有手机。有迹象显示,她的招聘者是一个人贩子,对方给Setia一个假身份证,并告诉她轻装上阵,不许携带手机和只带少量的钱。
她的姐姐曾经提醒她注意这些红旗,但Setia当时很自信,她也会说一些阿拉伯语,因为她曾在文莱当了六年的移工,也因此她能够供养女儿上学。而现在,她需要这份工作来支付她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她当下还告诉她姐姐,她相信该招聘者。
Setia忆述:“我告诉我姐姐让她不必担心,因为一切都会得到照顾。”Setia还称该招聘者为“Hajjah”,意指完成麦加朝圣的穆斯林的专属称号。
当Setia在新加坡落地停留后开始意识到恶梦的存在,她独自一人,感到很不安。她本想飞回雅加达,但她的身上仅有3万印尼盾 (2美元,约8令吉)。她开始意识到招聘者较早前指示她不要带很多现金,是为了防止她自己回家。
Setia懊悔说道:“我觉得自己很蠢,被这样欺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像我一样没有受过教育。她必须成为一个聪明的女人。”
当时Setia持旅游签证到了摩洛哥后,便立即向雇主抱怨她的工作安排明显是不合法的。但她的雇主出示一份他们签署的合同,合同上显示了她的签名,而这个签名是别人伪造的。她说,当时这些雇主支付了3000美元 (约1.25万令吉),将她从印尼带过来摩洛哥。雇主没有按照招聘者的承诺每月支付350美元 (约1470令吉),而是支付给她230美元(约965令吉)。
印尼移工家庭协会的协调员Marni Sulastri表示,Setia的案例已不是一个独立案件。因为在疫情期间,Marni Sulastri已经处理了4起贩运到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案件,在疫情爆发之前,每年这类的案件数量平均为十多起。
为了协助遣返被贩卖的移工,该协会采访移工的家人,并联系幸存者以确定事件的时间线,然后再向印尼政府报告有关事件,以寻求遣返救援行动。
Setia表示:“好在我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我的雇主。”她从雇主那里借到了一部手机,并与女儿联系,女儿随后再联系印尼移工家庭协会寻求帮助,事情才得到了解决。2020年11月,在印尼驻摩洛哥大使馆的协助下,Setia终于回家了。
她不禁感叹:“但那些没有经验和被雇主恐吓的人怎么办?他们最终又会去到哪里?”
2020年12月,Marni Sulastri正在协助一名被贩卖至叙利亚的印尼妇女,惟该协会在设法将她救出来前,双方便失去了联系。直到2021年1月,《华盛顿邮报》报导指出,数十名菲律宾妇女被贩卖到叙利亚后被困在那里。
在一项旨在保障移工的措施中提到,印尼自2015年起禁止移工在中东和北非的19个国家工作,当中也包括摩洛哥。正如Setia案件所表明,该禁令未能阻止人贩子犯案,并促使他们规避限制。2021年10月,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2015年的禁令应该取消,并列出了一些移工通过非法机构被贩卖到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案例。该委员会和国际移工联合会等提倡团体也表示,该禁令限制了劳工的移民和工作权利。因此倡导者们呼吁印尼政府批准并实施国际移工组织(ILO)关于移工和移工迁移的相关公约。
菲律宾是东南亚唯一批准国际移工组织2011年《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公约》的国家,该公约规定关于工作时间、工资、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的最低劳动标准,并为工人提供保护,免于遭雇主和招聘机构虐待,该公约肯定了工人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这是一门生意”
由于没有事前的经验或像Setia这样有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许多身在沙地阿拉伯的越南移工多年来一直遭受奴隶般的条件。疫情期间缺乏可遣返的航班,使本来就很遥远的逃离机会变得更加遥远了。
中东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主要受卡法拉制度的制约,该制度要求雇主充当移工的担保人。沙地阿拉伯对移工有一些严格的卡法拉规定,而这些规定是阻止他们在没有担保人的许可下离开该国或更换工作。
这些规定导致了遭受虐待的移工难以逃离其雇主。雇主通常会没收雇员的护照,有些雇员甚至被拒绝使用手机。对于在沙地阿拉伯大约100万菲律宾移工中被虐待的案件,海外菲律宾工人联盟 Migrante International呼吁菲律宾政府援助遣返回国。
海外菲律宾工人联盟主席表示:“大多数运动和要求都是针对菲律宾政府,因为他们与东道国政府有外交协议。”
但是在越南,公民社会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可用的资源也很少,招聘机构应该保护他们送往海外的移工。然而,来自越南和其他向国外输送大量移工的国家的证据一致表明,招聘机构往往都支持雇主和剥削移工。
该联盟谈到招聘机构时表示:“这是一门生意。”,“他们的首要任务永远是通过招募移工获得利润,这一点已经通过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证明。”
在沙地阿拉伯,有位妇女被一个不允许她离开的雇主困住,而且无法确保有航班返回越南,情况也越来越糟糕。妇女向New Naratif媒体透露,去年2月,她身体不适要求休息一天,却因此被雇主将她锁在屋外四天,且也不给她饭吃。
为了监督无良的招聘机构,越南已经实施了一项罚款制度。根据前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在2007年至2015年期间,移工部吊销了46家公司的执照,并对76家中介进行了罚款,总额高于3亿盾(13000美元,约5.45万令吉),平均每家中介不到175美元(约735令吉)。
人权律师Tran Thu Nam表示,这些措施几乎无法阻止中介延续虐待循环的恶习,他在2017年帮助从沙地阿拉伯遣返了一名遭受雇主长时间工作和身体精神虐待的移工。
他说:“海外移工部只关心征收罚款,而不是提供任何补救措施。”他也指出,海外的越南工人不属于越南的移工总联合工会。
Tran Thu Nam因此不再为移工做无偿的工作,但在第一个成功的案例之后,他被移工们的请求淹没,移工们以他们受伤的照片来向他求助。
“这太伤人了。我没有力量支持他们所有人。”
海外移工部确实监督著一个基金,其出资者包括工人和招聘机构,该基金的目的之一是支付遭受虐待的工人的遣返费用。然而移工部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基金不包括工人面临的许多风险,包括与流行病、战争和经济衰退有关的风险。该基金最多只能支付500万盾(220美元,约920令吉)用于遣返遭受职业伤害的工人,而该部认为这一数额“太低”。
基于缺乏政府的保护,许多绝望的越南移工转向社交媒体上寻求回家的帮助。几乎每周都有新的帖文出现在生活在沙地阿拉伯的越南工人群组中。H'Tai Ayun和其他8名被困在利雅得驱逐中心的妇女就是在这里发布视频。
Lan多次在面子书上发表言论以减少孤独感。去年6月,她用一个匿名账户登录发布:“大家好!这里有谁曾经喝过卫生间的水?这里有谁曾经不得不喝过厕所里的水吗?对我来说,这已经是第五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坐上回家的飞机。”
她最终受够了雇主,便决定拒绝工作。唯有在雇主于7月找到替代移工后,Lan才被允许正式辞去工作。她的招聘者承诺她将乘坐9月初的遣返航班回国,并说服她在那之前为另一个家庭工作。
“他们又把我卖了。”她说:“这个雇主比较好,但我的睡眠时间很少。”她补充,她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午夜。
与那些被困在驱逐中心的妇女不同,Lan仍有力量长时间工作,这至少可以为她赚到钱,让她寄回家。但她对来到沙地阿拉伯感到后悔,渴望回家看望家人和休息。
她一再坚持,她的真实姓名和她招聘者的姓名都不能在媒体上透露。
“否则,招聘者将永远不会让我回家。”
备注 : 此专题报导为战争与和平报导研究所(IWPR)支持的SEAFORE东盟精英项目(SEAFORE ASEAN Masterclass project)之一。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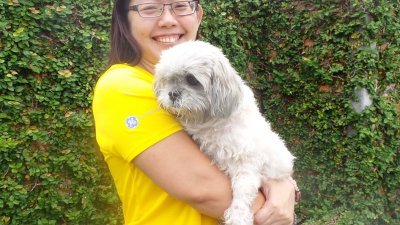







_1.jpg/fc5c863f3c2c8131df432aeb1ccc5bc8.jpg)
.jpg/a3fb65fc0555f9ffcab8bfab7c7458ea.jpg)
.jpg/77f2d79ee72b3079c7aaac9ca2231a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