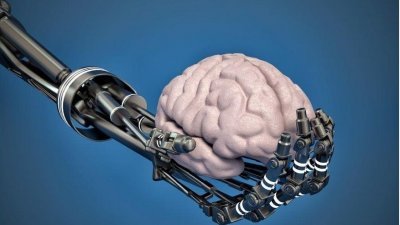当我从人类起源地──非洲回国,开始担任亚洲大历史协会的东南亚协调员后,我就忙著著手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马的大历史该甚么写?它的根基在哪里?我冥冥中仿佛感觉到答案就落在“殖民”和“反殖民”这两个关键词里。
无论“殖民”和“反殖民”之间,谁对谁错,谁在放纵和谁在驰骋,“殖民”与“反殖民”之间的相连、相牵,必能在虚寂中各取所需,而找到大马人能最终在大马落叶归根的大历史根基。
即如《庄子·天地篇》所言:“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若我此话让读者觉得属虚,是哲学的范畴,那马来电影《Mat Kilau》能称霸大马票房冠军就是铁定的事实,属实。
出于此实,也出于彼虚,多年前我答应了Cik Srikandi (一位在大马隐名埋姓的马来同胞历史作家)为她的书《刚线脉、水银血》(Beruratkan Dawai Berdarahkan Raksa)写了其中的一篇序言。
根据大历史的记录,宇宙从一开始,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殖民”与“反殖民”之战,无不在每一刻、每一时重演。造物者创造了一个平衡的世界,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宇宙中的物质(matter) 和反物质(anti-matter)必须具有相同的数量。奇怪的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无论是地球上最微妙的生物如细菌,还是外太空最大的生物如恒星,几乎完全是由物质构成的。反物质去哪了?也就事说,我们,甚至宇宙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为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平衡、斗争及再平衡、再斗争,而产生。
人世间也是如此,“殖民”与 “反殖民”之间的斗争永不止息。每一个生物,从最小的细菌到最大的恒星,包括人类本身,总是热衷于寻找新的领域来殖民或探索。
当然,在新的殖民领域中,还有其他长期定居在那里的生物。作为回应,被殖民部落当然也会为捍卫他们代代相传的领域,自然而然地对殖民者进行激烈的抵抗。殖民者也是如此,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对刚刚努力殖民的新世界的所有控制。他们将战斗至死并发动一连串的反击,以永久控制他们刚刚征服的新世界。随之而来的,是殖民运动和反殖民之间的交替、争锋及震撼人类世界的场面。
最好的例子是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的航行,它催生了在大西洋快速吹拂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变革之风”。这阵“风”与欧洲各国主导的殖民和贸易领土的扩张有密切关系,最终扭转了农业革命(Agriculture Revolution)时代。
在这阵大风吹起前的近一万年的时段里,农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在容纳了除欧洲文明以外,还有其他主要位于美洲、印度次大陆、马来群岛、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中国和非洲的农业文明。随著非洲和美洲的新殖民地及贸易区里的农产品、家畜和人力资源被这阵“变革之风”强制动员或进行大规模交易,农业革命的时代意义也变得越来越失去导向,最终在近乎不到300年里,被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完全取代。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强迫劳动为欧洲大陆带来了“欧洲恩典之雨”,也为他日欧洲人的“进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将欧洲国家列为人类伟大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殖民部落,而无视人类自20至 30万年旧石器革命(Paleolithic Revolution)开创以来所享有的成就。
在短短不到300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开创的工业革命时代,不仅见证了倍增的奴隶、人力资源剥削,而且还看到了以国家建设 (nation building)的名义对全世界环境“宣战”,而造成的破坏,国家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或 nation-state)也随之倍数的急剧泛滥。在工业革命时代之前,无论是农业革命还是旧石器革命时代,人类仍然是适可而止的,在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之间保持著健康的平衡。他们渐进的、谨慎地扩大人类的可控范围,土地使用覆盖率和人脉网络。
不幸的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欧洲殖民者已经失去了理智。为了成功战胜长期统治地球的其他农业大国,他们开始抛开他们古欧洲祖上的智慧。更可悲的是,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在摆脱欧洲殖民者的统治后,也步其前殖民者的后尘,以更可怕的速度继续大规模破坏人类与大自然的平衡。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将欧洲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国家建设” 和“国家民族主义”的框架作为摸仿和想像对象,以幻想像前殖民者一样占据高位,并恢复他们在农业大国时代的荣耀。
锡克教徒联合会的马来西亚分会在公开谴责《Mat Kilau》电影沦为把其他族群描绘成“反派”及批评此电影可能导致本国种族和宗教关系不和的同时,也应邀请本国多元种族和宗教信徒一起来反思:让我们不要再掉入欧洲殖民者所输入的所谓“国家建设” 和“国家民族主义”的陷阱!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