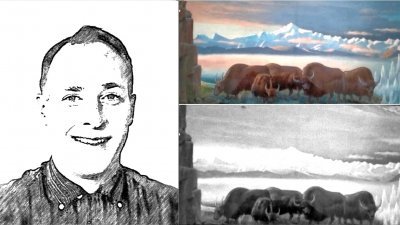10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上,美国牵头提交的一项涉疆问题决定草案遭到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强烈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并非美国首次操弄“涉疆”议题,而实际上,“涉疆”问题早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工具。更值得重视的是,在美国主导操弄“涉疆”牌的庇护下,以“东伊运”为代表的好战分子、恐怖主义组织也正如流毒一般在东南亚以及国际范围内蔓延,美国操弄“涉疆”牌所带来的公共危害同样不可小觑。
众所周知,“涉疆”问题并非一个新话题,本质上是反暴恐、反分裂、去极端的问题。为了持续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中国政府在新疆坚定依法开展以“去极端化”为主要特征的反恐工作,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维护国家统一、安全与民族团结,进而为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创造有利条件。
从横向来看,这一做法与其他国家“去极端化”、“去激进化”的政策并无二致,例如马来西亚的“去极端化”、印尼的“去激进化”。这在根本上是各国对“极端化”引致恐怖主义、暴力和极端主义后果共有认识的逻辑结果。对此,2018年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明确将“极端化”定义为受极端主义影响,渲染偏激的宗教思想观念,排斥、干预正常生产、生活的言论和行为。
由此,为了有效应对“极端化”,中国在“去极端化”政策引导下,采取一系列具有预防性为特征的举措,针对极端分子进行宗教观念重塑与再教育,以用来纠正对宗教和政治上的误解,从而有效祛除极端思想,实现极端分子的有效转化与回归正常生产、生活,进而减少恐怖活动发生的可能性。
然而,在现今美国主导的舆论中,“涉疆”问题却成了民族、宗教和人权问题。这在过程上是美国政界、媒体和部分学者、智库多方共同操弄的结果。在“涉疆”舆论中,新疆本身并非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涉及到民族、宗教和人权等相关议题的一系列概念和字眼,例如所谓“强制绝育”、“强迫劳动”、“种族灭绝”及“集中营”,才是美国官员、学者和智库及媒体聚焦和程序性操作的著力点。
美国官员所谓的“权威”、“吸睛”和学者、智库表面上的“独立性”、“专业性”,与美国媒体传播力“一拍即合”,在国际传播中形成了美国在“涉疆”话题上的议题设置、内容传播和情感塑造的主导地位。而在战略上,这是美国长期奉行“以疆制华”的结果,是美国自1997年启动“新疆工程”以来所一直希望看到的。
如今,随著美国日趋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涉疆”牌的工具性更为凸显,“涉疆”牌是美国对华奉行战略竞争和遏制中国的著力点。一来,“涉疆”牌还包括著美国奉行对华经济“脱钩”的做法,例如通过炒作“强迫劳动”等极具价值观色彩的概念直接影响了部分国际行业协会、意见领袖、商业精英和公众的态度,以实现打击新疆产业经济发展和对华经济“脱钩”的目标;
破坏中国国际形象
二来,“涉疆”牌还隐含著美国破坏中国国际形象和影响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目的,“涉疆”作为一个敏感的神经元,深刻影响著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对话、合作关系。
国际社会不仅应该对“涉疆”议题的发酵过程及其工具性有清晰认知,更须把握这一议题发酵所带来的公共危害性。这首先就表现为对中国和有关国家间友好对话与合作的破坏。
由于宗教的原因,美国所主导的“涉疆”话题和议程在一部分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度)有著一定的市场,部分民间舆论与学者、官员基于宗教情绪和政治需要附和欧美舆论,部分保守势力、智库与极端分子甚而接受欧美资助追随炒作“涉疆”议题。
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友好对话与合作由此难免受到破坏,其中就涉及“涉疆”极端组织和个人的窜访。在美国等国的庇护下,“东伊运”组织及其成员在国际范围内还有著可见的活跃度。例如,该组织的领导人黑达依吐拉曾在今年9月上旬到马来西亚窜访并会见了美国驻马使馆官员,马来西亚国防大学教授穆罕默德米扎姆(Mohd Mizam)就此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明确谈到,马来西亚应从马中关系的大局考虑,避免接受这类有争议人物的到访。
其次, “东伊运”及相关持有暴恐思想、极端思想的组织和个人在国际范围内的流散直接危害了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这也包括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内。一方面,由于地理临近, 东南亚地区成为“涉疆”暴力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个人转向其他地区的中转站或寻求庇护之地,东南亚部分国家因此不得不直接面临著这方面的安全挑战。
一旦他们流散受阻或在自恐布组织“伊斯兰国”(IS)回流,就地“圣战”自然成为选项,泰国、土耳其等国都曾深受其害;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人员还与阿布沙耶夫等东南亚本地恐怖主义组织存在勾连,寻求就地发展或成为地区恐怖主义组织网络的一部分。无疑,这势必将给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区国家带来新的长远威胁。
对于此,中国和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应避免被美国所主导的“涉疆”舆论误导,立足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立场和“去极端化”反恐的共同认识,就有关议题加强有效对话。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