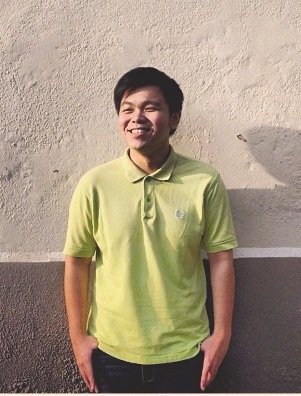一路上细雨濛濛,雨水打在车镜上,听不见嘀嗒嘀嗒的声音,却看得见形迹,像一朵朵的花掉落在车镜上,显露出盛开的那一刹那。雨刷没有怜花的美德,它无情地把一朵朵盛开的花扫开,碎落满地。我坐在车子里幻想著,笔直的道路上,到底有多少多花瓣被无情钢铁怪物一辗而过,只留下唏嘘。转过无数的弯,踏过无数的残花,车子忽然轻跳了起来,再掉落地面。车子轻跳起来所造成的震动像晨曦一样,带来了温暖的感觉。这一刻,我知道离家的路不远了,就在下一个转角。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时分,走下车子的那一刻我发现停车场里多了一些盆栽,这些盆栽相貌奇特,是我从未看过的,于是我便像个小孩发现了新天地一般,让自己的眼睛紧紧贴近著这奇怪的盆栽,试图从中看出个所以然来。然而,我看了许久,却依然看不出这两盆怪形状的花朵是什么模样,这时父亲走到我的背后,轻轻地向我的肩膀拍了两拍。
“这两盆东西叫小鸟花。”父亲说道。
小鸟花?好个简单易懂的名字,可是在父亲道出它的名字之前,我压根儿看不出这两盆植物哪里长得像小鸟,可现在我看出来了。其中一盆的花朵是以红色的“小鸟头”所组成,零零散散的,有些独立成家,有些则三五成群的围在一起。另一盆感觉上更壮观了,如果花朵开得漂亮,你直接可以看见一只绿色的鸟站在两片花瓣之中,像是被保护著的一样。然而这一盆植物也生出了不少异形,你可以看见除了绿色鸟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生物站立于两片花瓣之中。
“是长得很像小鸟,哈哈。”
“这两盆花不只长得像小鸟这么简单,它还会引来真的小鸟,在这里唱歌。”
“这么厉害?有没有骗我啊?”
“为什么要骗你?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了,哈哈。”
像小鸟的花竟然可以引来小鸟?这是我自懂事以来都没听过的事,听完父亲的话以后,我是抱著半信半疑的心态来看待的。吃晚餐的时候,知道我喜欢摄影的母亲听见我和父亲的谈话以后告诉我准备好相机,因为我有机会拍到像《National Geography》里动物生态的照片。听完母亲的话以后,我发现我眼前这两个对我有养育之恩的人讲话的语气好像有一点儿戏,但却有著坚定的眼神,不禁让我对停车场里那两盆植物的兴趣进一步提高。
晚饭过后,天色转暗,傍晚那橙色的天空好像承受不起阳光的离去一般,将自己反锁在阴暗处,放弃了灿烂的笑容,掉下了一颗颗的眼泪。对于悲伤这一回事,天空的了解似乎还不够深入,因为它没有放开怀抱地大哭,却选择了以云朵作为掩饰,偷偷地、静静地向大地述说著它那说不出的悲哀。
我走到停车场,一边喝著母亲所煲的红豆汤,一边接受冷风的袭击。屋外的雨势越来越大,心想今晚无缘看见小鸟花引来小鸟唱歌的奇景了。红豆汤喝完了,身体稍微得到了抗冷的温度,然而内心却得不到滋润。曾经有人说过多愁善感的人很容易受雨天影响,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多愁善感型的人。雨声敲打在屋顶上,“啪啪”、“啪啪”地作响,雨声就像一首乐曲,不停的在敲打我的心房,让我的血管膨胀,刺激著我的大脑,使它翻箱倒柜地把已经尘封的物品像瀑布似的倾泻而出。我禁不住地想起几年前的那段让自己悲伤的恋情。我跨步走到盆栽前,在隔著铁篱笆的距离下,向它们倾述著这一段故事。
我的耳边传来了雨声以外的杂音,这些杂音来自我邻居的小孩。他们家在我家的左手边,而那一个正在吵闹的孩子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了,我们一家大小都称他为“肥仔”。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肥仔,因为这个年方十二的小孩有著球一样的身形,走起路来时,更有地动山摇之势。他正在闹别扭,原因是他妈妈不让他到外面去散步。
“你刚才又说让我吃饱饭后出去走走,现在又不给!”
“现在下雨了,你没看到啊,是想生病还是想吃藤鞭?”
他妈妈发现了我听见他们的对话,向我笑了笑,并对著肥仔说:“看!人家哥哥笑你了,还不快点进去,外面很冷啊。”我也向肥仔的母亲笑了笑,看著肥仔继续坐在他家停车场里,满脸通红地闹著别扭。
我回头看屋外被雨淋湿的小鸟花,它不会说话,而我也沉默了。肥仔的吵闹声似乎已经停止,但他并没有跟随他母亲回到屋内,反而拿了一张小凳子,静静地坐在一旁看雨。这时,我右耳听到了一些嘈杂声,我把头转向右手边也即是嘈杂声的方向,看见我的另外一位邻居一手叉腰,一手拿著电话,以他那洪亮的声音向电话的另一方争执著。我把身子稍微向右倾斜,以便听得更清楚。邻居是一位面铺老板,姓孔,是一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的面铺生意十分的好,这可以从他家里的轿车数量与日俱增看出。在这一个雨夜,他赤裸著上半身,正在与供应商议论著食材涨价的问题。
不知是逐渐变大的雨势抑或是邻居那洪亮的谈话声,住在我对面的马来叔叔也走了出来,站在停车场,把头探出篱笆外,从左到右,从面铺老板到我再到肥仔,以他那老花眼仔细地看了一番。我不知道马来叔叔的名字,只是会唤他作“Pak Cik”,从父亲的口中得知他是一名退休军人,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家里享受著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Pak Cik各自向我、肥仔以及孔老板打招呼,孔老板向Pak Cik 意思意思地招一招手后,就继续他与供应商的“拔河比赛”。肥仔则依然是坐在凳子上,一手托著自己的下巴,另一只手则高高举起向Pak Cik 问好。Pak Cik 最后把头转回来看著我,点起了香烟。Pak Cik在点完香烟以后,转身走了进屋,在他转身之际,他一面微笑一面摇著他的头,我似乎可以看见在他双眼旁边的鱼尾纹不断涌现,这除了是岁月的痕迹,也是熟悉的画面所带来的脚印。在同一个雨天下,Pak Cik 是第一个走回家里面的人,然后是孔老板,再来是肥仔。而我,则还是不断地对著小鸟花,倾述著同样的故事。
隔天一早,阳光打破了一整夜在哭泣的天空,把橘红色的光芒散播大地。我走到屋外,看到了父亲所说的奇景。两只黄身蓝头的小鸟正在花中嬉戏,把叶片上的晨露以及雨水轻轻地推向地面,把嘴轻靠向以红色的“小鸟头”所组成的小鸟花,就好像接吻一般。我拿著相机,走到屋外,希望帮它留下这一个美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