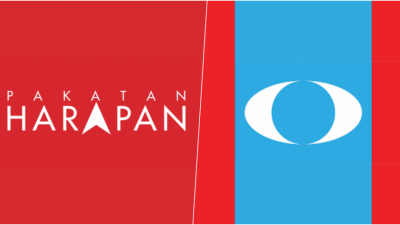“不能捞生的话,新年就白过了。”某次饭局上,听到朋友蹦出这句话。
他是土生土长吉隆坡人,父母的亲戚也全都在这座城市落地生根,所以字典里没有“回乡”这个词。
他也不特别羡慕过年有乡回这件事。对他来说,平日上下班已经塞得烦躁,要是新年前夕还需要花数小时在公路上龟速,那他宁可不回家,情愿一个人悠哉清静过年。
这当然是不成立且侥幸的假设。他还是很期盼新年能与家人朋友团聚,挣得几天假期,难得都城通畅无阻,他可以到处逛街或看贺岁电影,陪家人买年货,与朋友到向往已久的网红餐馆吃饭,这就是他的过年意义。
差点忘了,捞生不能缺,这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过年仪式感。
比起拿红包或吃团圆饭,他反而认为,捞生才是农历新年最有象征意义的传统。如果亲朋戚友无法聚集一起,在餐桌上拿起筷子翻搅著七彩鱼生,嘴里大喊“兴发旺”的话,就觉得这个过年少了点什么东西。
我笑他患了“非典型过年症”,他反驳认为这才是大马过年的特色。
“你想想,无论是拿红包或任何年菜,都是源自于中国过年的传统习惯,捞生却是马新一带才有的独特过年仪式。我们虽都是华人,但祖先飘扬过海扎根在这那么久,文化脉络早已发展成另一种独特的热带雨林文化。我们应该适时建立有别于中国的过年特色,而捞生就是一种属于大马华人的新典范。”他骄傲地说。
不过,疫情关系,群聚不受鼓励,更何况是在大众场合拿著筷子大动作捞生。因此,很多商家今年都避开这个习俗,许多家庭也都选择乖乖待在家过年,不像以往一定要捞生。
不捞生,还能做什么?这哪像过年?他最后丢下这些话,在我脑海盘旋很久。
明明还有很多东西做啊朋友,我说。
坦白说,我住在霹雳州小乡镇班台20几年,过年桌上从没出现过捞生,直到在吉隆坡发展后,才见识到捞生这回事,对我而言这反而有点像“次文化”,因此心态上倾向凑热闹大于文化融入,总觉得捞生就只是城市人过年的热闹噱头。
况且捞生只是短短几分钟的事,怎能就无限扩大成整个农历新年的代表意义呢?
对我来说,比起新年要特意做些什么,倒不如说与人的连结才是重点。尤其经历长达2年的疫情后,人事已非,旧俗已淡,连发达的科技有时都弥补不了某些人分离的事实。
与家人好好吃顿饭,与朋友好好聊一聊,与伴侣好好抱一抱,比起钞票,这些都是无形的红包。若懂得兑现,价值才彰显。
心里放著这些事,新年才万事如意。
“还是不太一样啦。捞生时嘴里喊著各种贺词,感觉才比较踏实,一整年运气也会比较旺。”朋友对捞生的执念非常强大,我怀疑他的血液里早有这种迷信基因。
开年总要有好彩头,这点我能理解。我说。但运气这回事,与其说是来自一道菜的咒语念力,倒不如说与平日的习惯与念头有关。
与其不断希望心想事成,倒不如先学会感恩转念。凡事多一份耐心,可以负面思考,但别放弃出路。这就是好运的基本开关。
疫情毫无预警地侵袭,为的就是带给全人类下个时代的新思维。好多传统习惯,早已被冷酷无情的疫情清扫得荡然无存,去年甚至连简单的过年回乡都可以牺牲,在病毒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坚持?
就只有正念与珍惜。
这才是过年的最好祝福。心存正念与珍惜,不用特别仪式,天天也能像过年。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