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自由业译者不自由》这本著作,一向在电脑荧幕前默默耕耘的谢丽玲进入大众的视野。她能运用9个语言组合做翻译,是不可多得的多语人才,也充分表现大马人在多语环境下所练就的语言灵活度。她把多语优势看作维生工具,但事实上,语言不通的人透过她的转换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多元民族的和谐,有著极大的帮助。
英中、中英、英巫、巫英、中巫、巫中、日英、日中、日巫,谢丽玲能应付9种语言组合的翻译工作,这样的能力和能操多种语言略有不同,一如拉曼大学日语讲师兼翻译者叶蕙在《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的序文里提到:“如她(谢丽玲)所言,语言能力只是当一名译者的基本条件,语言能力好的人不一定能当好的译者。因为翻译不单只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还在乎各种专业知识,对事物的感知、观察、分析与判断能力。”译者需要消化原文,并在保留作者风格的前提下,将内容以另一个语言呈现,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大马人经常以懂得多种语言而自豪,但即使有这样的环境,翻译领域却没有格外蓬勃,谢丽玲指:“有好书出版,台湾、日本的出版社很快就会著手进行翻译,据知印尼也是这样,但或许正是因为大马人精通多语,通晓中英文,也读得懂马来文,能直接阅读原文书,因此反而不注重翻译。”她接著说:“不过,在大马从事翻译有个好处,就是不需要特定的认证或执照,不确定自己是否要走这条路的人可以先尝试接一些案子。”
谢丽玲2006年担任全职译者至今,冲著“全职”这两个字,常常有人会直接用“专业翻译员”来形容,她认为:“专业不是用全职或兼职来区分的,而是用作品的素质还有工作的态度。”当然,经过十多年的磨练,现时的谢丽玲在业界里是有口皆碑的名字,但她强调:“就算是副业,只要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好的,那也是专业。有些人可能是这个领域的天才,只不过他有其他更想从事的职业,而把翻译当作偶尔客串的兴趣。你不能说他不专业。”

既然提到了“其他更想从事的职业”,此前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她笑说自己从来没有当全职译者的规划,“从事翻译是为了维生。我有想过出书,但明白全职写作难以办到,不是每个人都能靠版权费维持生活,尤其像欧大旭(Tash Aw)这样,原稿可以卖出高价的更是特殊例子。相比之下,翻译工作的机会较多,酬劳也比较好。”编按:欧大旭是大马籍作家,赴英国剑桥大学修读法律并于当地执业,处女作《和谐绸庄》即获得惠特布列首部小说奖(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
为日文杂志撰稿 介绍大马文化
谢丽玲当初在理科大学(USM)念的是化学系,后前往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攻读硕士学位,主修比较民主化。“我没有翻译的理论背景,但有阅读的习惯,大多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她也为日文在线杂志《Malaysia Magazine》写专栏,为了介绍和大马相关的文化,特别去接触本土电影、书籍和乐器,她透露早前看了本地知名跨性别艺术家兼作家蕾吉娜依布拉欣(Regina Ibrahim)的文学作品《Perjalanan》(路程),“身为穆斯林,变性人肯定是被打压的,但她在文中提到‘我会努力,其他的交给阿拉。’她虽然变性,但信仰还是在那里。我是无宗教信仰的人,却深深感受到人只要可以把偏见放下,就能看到平时看不见的美。”
她有感:“语言掌握得好,确实可以让你进入不同的世界。但不得不说,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之一,却不是唯一的工具。”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她认为网络世界里的吵吵闹闹正是因为有人在语言上文字里挑骨头,“很多问题来自字面上的偏见,因为单方面的错误诠释造成误解。”语言和文字是双面刃,用得好利人利己,用得不好则有可能害人害己,作为一名翻译人,谢丽玲自认没有多大的使命感,却也认同自己是一座桥梁,“就是有小小能力,把这一边和那一边基于语言不通而被分开的人连接在一起吧。”

想离开城市、做比较“简单”的工作
时间和金钱都是消耗品,但偏偏大部人得花时间换取金钱。谢丽玲也有这样的困扰,为了维生,必须把一些时间预留下来。当初之所以选择成为自由工作者,理由很直接干脆——懒得求职,“离职前的几份工作都和文字有点关系,闲赋在家时,凭著之前建立的人脉,陆续接了一些翻译的案子。”她坦言:“我用了大概3到4年的时间才真正稳定下来,间中遇到工作量大减时,也曾想过如果真的无法维持,那就找工作吧。但现在十多年过去,说实话,很难再回到职场。”
她很清楚,每一份工作有喜欢的部分,自然也会有不喜欢的部分,“大部分人觉得自由业者就是没工作,但自由工作的人,无论是程式编写、文字抑或设计工作者,都深深了解当中的难处。我们其实有非常忙的时候,东西会一直发过来,有无数的‘死线’(Deadline)要赶。”她接著说:“遇到有趣的内容,自然就做得特别开心,但大部分时候,是案子选我们,而不是我们选工作。除非你是很有名的译者,能长期翻译同一个作家的作品。”
谢丽玲笑称自己只要把工作接下,便会全力以赴,但这么多年下来,也学会了衡量自己所能负担的工作量,“工作生活平衡还是很重要的,健康要顾,也不能因此失去自己的人生。”她坦承:“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现在的工作相当辛苦,对眼睛造成的负担尤其大。而且我想多花时间在写作,翻译的工作挺重的,身边的杂事也多,在城市里很难专注,想搬去乡下,专注做自己想做的事。”
为了打书,到大专院校分享时,最常被问到若想从事这一行,要如何开始、怎样接到案子,无论是分享会现场抑或现时接受访问,谢丽玲的回答都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美。”她说:“自由译者养活自己是可以的,但如果想赚大钱,还是考虑做生意吧。年轻人刚毕业如果没什么负担,也不是特别注重物质、会花钱,一开始工作量较少,赚一点点也能生存下来。但我的建议是新鲜人还是先去体验职场,累积一些人生经历才来接案子吧。”

独自作业 也与人交流
自由工作者没有同事,大部分时候必须独自工作,所以有说,要成为自由译者首先得耐得住寂寞。但谢丽玲刚好就是非常享受独处时光的人,“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用自己的步调生活。当然,有时候还是会遇上需要团队合作的工作,我就把它当作新尝试,坦然地去接受。”然而,她不讳言:“很多时候,是因为处于骑虎难下的状况,是被迫的。还记得第一次到电台接受访问时,我抱著战战兢兢的心情去,但完成任务后,那种又一个挑战被解锁的感觉,也很不错。”
有纪律,才有自由
虽然无须打卡上班,但谢丽玲还是给自己订下上班时间,“早上10点到傍晚6点是我的工作时间,当然,这是有弹性的,可以更动。重点是生活作息要有规律,妥善安排时间,也唯有了解自己的作息,你才知道案子能不能接,能不能准时完成。”
靠固定客户稳定财务
自由工作者没有固定的月薪,也没有公积金等其它保障,若是财务管理不当,只要工作量减少,很容易就陷入窘境。十多年来一直是自由身,谢丽玲这么说:“要维持财务稳定,就必须有固定的客户,他们给的价钱或许不是最好的,但一直有工作给你。”她坦言:“即使有固定的客户,你也未必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把工作发过来。有时遇到其它机会,比方说书籍翻译这类比较耗时耗力的工作,当下时间不允许,也只好推掉,因为若是没办法应付还硬接,最后只会两头不到岸,失去对方的信任。”
收入虽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信誉更不能丢失。她指,自己也曾遇过好几个月没有钱进帐,但幸亏也不是太花钱的人,只要有储蓄的习惯,还是能应付。“我很喜欢旅行,只要有钱可以旅行,就觉得足够了。”

身为大马人,其实很幸运
因为语言学习和工作的关系,谢丽玲认识不少在大马生活的日韩裔,“当然,他们大多是被大马的多元给吸引,才会过来生活,也或许没有真正接触到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很羡慕大马人。有一个韩国人是这么跟我说的:‘当初你的祖辈选择在大马定居,你不觉得庆幸吗?’”对方的意思是,生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不似他们活在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的环境,更有利于学习语言,尤其是他们一直努力学习的英语。
谢丽玲不否认这一点,“我们从小接触多语言,确实有学习语言的优势,学起来比较轻松。”她举例:“台湾人问我订书机的英文怎么说,我随口说出答案,她觉得很羡慕。但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用到这个单词,他们却不是。去菜市场,她问我:‘这些菜,你都能说出它们的英文吗?’包菜是‘Cabbage’、花椰菜叫‘Broccoli’,这些我们平时就在用的词,它们要抱著字典死背硬记。”光看这一点,你能说身为大马人不幸运吗?
谢丽玲笑言:“我是比较内向的人,讲座、分享是超出我舒适圈的事。但没办法,要宣传新书,不然对不起出版社,所以把它视作新的挑战。”图摄于今年中旬举办的海外华人书市。
问谢丽玲最近在读什么书,她说:“之前看了《人类大历史》,现在看著《人类大命运》(Homo Deus)。”她认为,读文科的人应该尝试看一些理科的书,理科背景的人也该尝试接触文学类书籍。阅读未必得和自己的工作领域有关,读一些杂书对激发思考很有帮助。
《从国际新闻现场到自己的房间》是谢丽玲的第一本著作,她透露:“出书是梦想,我喜欢旅行、喜欢文化,喜欢听当地人说故事,在出版社找我写书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要以译者的生活为题材。”对她来说,自由译者的工作其实挺单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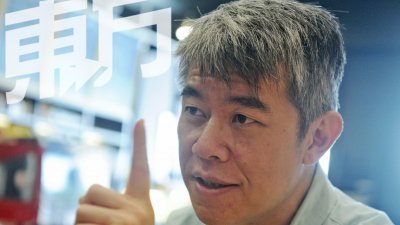

.jpg/572745570abaf4cc3969e6a0095d6ae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