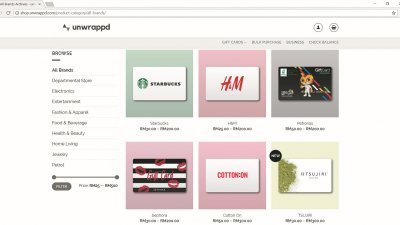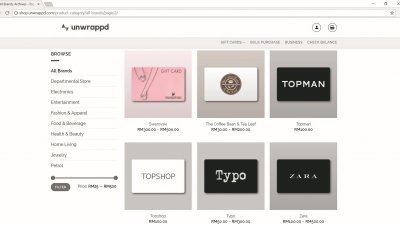曾担任建国日报芙蓉记者、周刊娱记、恩嘉唱片公司助理制作人、宝音唱片宣传、词曲创作人、幕后合音的艾浠汎,1987年出走英国伦敦,在当地邂逅了丈夫,1989年在彼邦结婚生子后,淡出璀璨的娱乐圈,专心相夫教子。2017年,她为重出歌坛的歌手郭晶丽写了一首《我想你了,你知道吗》,入围《娱协30》“最佳经典流行歌曲”;而且她也升格作家,即将推出第一本书《花城往事—梦里的新年树》。
1985年,22岁的艾浠汎为歌手康乔写了一首《脱下指环之后》,初试啼声的她即拿下《星丽奖》十大冠军歌曲,在娱乐圈展露头角。之后,她陆续替康乔、张国祥、邓智彰、江梦蕾、罗宾等歌手谱曲填词,其中张国祥的《墨镜后的眼睛》,还摘下“1987年第一届娱协奖十大歌曲”。

淡出娱乐圈30年,何止年轻一代相见不相识,对艾浠汎来说也恍如隔世,“其实没有复不复出,我从不觉得自己是重要人物,我最喜欢的身分还是当记者。”
艾浠汎20岁入行当芙蓉地方记者,之后转往明星周刊娱乐记者,开始接触五光十色的娱乐圈。从小爱写写唱唱的她,音乐天赋很快得到赏识,“有天我在宿舍里写歌,同房好友说很好听,鼓励我拿去唱片公司试一下,我把歌曲录下来,交给了新组合唱片公司老板叶啸,他是康乔的老板。后来我的处女作《脱下指环之后》拿奖之后,越来越多人找我写歌。”
24岁那年,她买了一张机票独自飞到英国,想要给自己一个学英语的环境,“有次访问李小龙的儿子,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可惜英文不灵光,不能够顺畅地表达。”她顿一顿又开口,“其实这只是导火线,我的个性就是坐不住。”原本计划去两年,谁知道在当地邂逅了丈夫,26岁在彼邦结婚生子。
诚如艾浠汎所说,她是个坐不住的人,在英国相夫教子之馀,她还重返校园念了幼教、室内设计、考获酒保资格,甚至于今年初加入英国慈善团体“Medical Justice”担任中文翻译员,为被英国移民厅拘留的华人争取应有的医药治疗。

痛苦的时候就去学习
生活看似充实,艾浠汎却说,每当处于人生低潮的时候,她就去学习新知识,或是找一些事情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尤其在异乡生活的日子并不容易,语言是很大的障碍,她意识到自己在儿子学校的劣势处境,“去接孩子时,其他家长不跟你交谈。”为了给儿子树立好身教,也不想儿子在学校被孤立,她重返校园报读幼教课程,并且在当地的私人幼儿园担任幼教。
2006年,她与丈夫一同创业,在克莱顿经营中餐馆,为此她努力啃书,考获酒保资格。2011年,她原本计划好返马陪母亲过农历新年,可是因为餐馆工作延误了几天才上机,没想到母亲突然病倒,等她赶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陷入昏迷,年初十在医院离世。“如果我不是为了做生意,就不会错过与母亲的最后团圆。”语音未落,她的眼眶一热,哽咽得说不下去,赶快抓起桌上的纸巾往眼眶扇呀扇,不让眼泪落下。
24岁远赴英国定居,让母亲承受著生离的思念与煎熬,艾浠汎自觉对母亲亏欠太多,母亲离去后,她对中餐馆的生意意兴阑珊,又跑去报读了室内设计课程。“心里有太多的痛苦无处宣泄,我只想挑最难的课程,把自己去抽离出来。”加上儿子长大搬离家,她的内心空出了一个大洞,于是她开始执笔写书。
艾浠汎提起手比划出波浪形状,正如她的人生高低起起伏,“有时候我也会问天,还要考验我什么。”

不放弃,人生充满可能!
2018年是艾浠汎的人生转捩点,她终于下定决心结束餐馆的生意,在感情上也去旧迎新。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开始担任英国慈善团体“Medical Justice”的中文翻译员。“英国还是一个很人道的国家,很多的被拘留者不是难民,而是经济型的寻求庇护者,英国不会贸然将这些面对生命威胁的求庇护者遣返回国,他们在拘留所内可能会生病或是长期拘留可能会出现精神状况,这个慈善团体就是为被英国移民厅拘留的华人争取应有的医药权利。”
当翻译员是需要文凭资格,但是当局却破例采用艾浠汎,“他们看过我的履历,知道我当过记者,人生经验与阅历看起来可以帮到他们,逐派了第一个个案让我试试看,结果他们很满意,直接聘用我当翻译员。”
艾浠汎至今接了5个个案,“最近我接了一个个案,拨通他的电话以后,他说我们来得太迟,他已经被遣送我回国了,听了挺心酸的。”这也提醒她要当个称职的翻译员,这个工作直接对于个案能够继续留在英国起著关键性的影响。这份工作的酬劳不错,加上工作时间够弹性,保障了未来的生活。原以为这辈子与爱情无缘了,最近也也找到了答案。艾浠汎说:“我向来遇到问题,都是求生不求死,人生只要不放弃,什么都有可能!”

为父平反 尘封旧事成书
这一次艾浠汎返马,除了出席《娱协30》颁奖典礼,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为酝酿多年、即将出版的第一本书《花城往事—梦里的新年树》与媒体见面。
她在书中的自序里写到,为了写这本书,翻起许多尘封旧事。那些成长岁月的往事,一直搁在她心里的小角落里,她说:“我想写很久了,可是很多事情终究要讲时机与缘分。”
艾浠汎写这本书是因为父亲。她说一生受父亲的影响很深,“父亲参与很多教会服务,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就放我上台表演唱歌,我的胆量是这样训练来的。”父亲交给她一生受用的东西是自信,“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来的,他总告诉我,我有能力完成任何事。”
她从父亲的生世说起,“我的祖父是厦门米商,他经常往返新加坡经商,我父亲在新加坡出生,他妈妈在他3岁时过世后,祖父续弦,后母对父亲不好,所以他随曾祖母回厦门定居念中学。”
“父亲在中国沦陷前,从厦门回到新加坡,在德光岛小学教书,后来日军南侵,父亲参加抗日活动被逮,在被押送枪毙途中机警跳车逃入山芭,被游击队抓到,经查证之后确定父亲不是奸细,就被送往芙蓉当‘暗底’。”
抗战结束后,她父亲邂逅了母亲,自此在芙蓉落地生根。1948年,父亲替教会创办了“圣玛丽中英小学”,因为资金有限,起初学校办在教堂附近的简陋木楼里,直到1951年有位善人捐出5.75亩的橡胶园地,在教会的支持下,花了几年建立了“新中英小学”。艾浠汎说,“在新校成立后,心胸豁达的父亲让出校长的位子,自己退居副位。有次学校一笔建校基金不见了,教主前来调查的时候,这笔账就被赖在我父亲头上。”
后来,改名校长利用公职权把艾浠汎的父亲调走,“那时候父亲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她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一家人学校宿舍住了十几二十年,父亲花了很多心思开垦,把荒地变成一座农场,在我印象中好像做戏那么美,而且应有尽有,结果我们被勒令在两个星期内要搬离这个家。”她的父亲在8个月之后心脏病发,没多久就走了。那年艾浠汎才12岁。她一直都对父亲的郁郁而终耿耿于怀,“父亲搬出来以后整个人都失去了光彩。”她不讳言,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要替善良的父亲“平反”。






_2.jpeg/83a1b58bfd021875f39a10dd978eff23.jpe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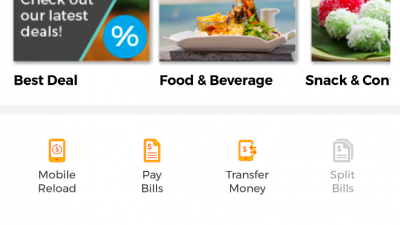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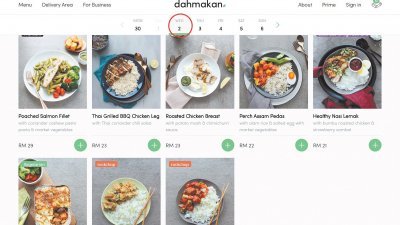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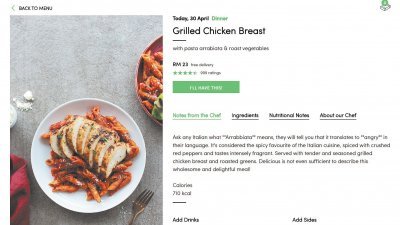






.jpg/131470bdcc84bec2184108dbe8137f5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