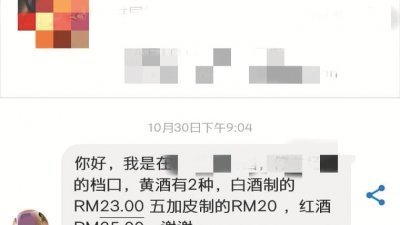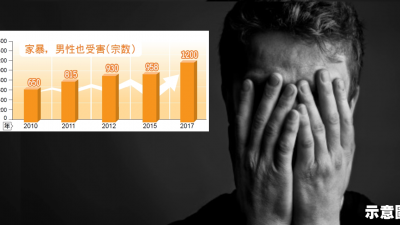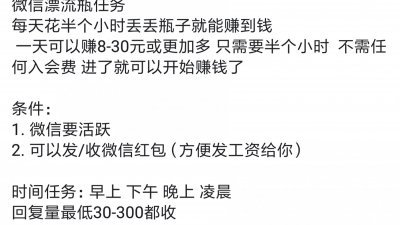继柔州金金河化学污染事件爆发后,再度敲响了河流及水源污染的警钟,但我国在对抗毒河的整体情况似乎未有多大改善,国内各地依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传出工业废水污染河流的事件。
其中包括上霹雳宜力雷河出现致癌物质——砷、柔州文律河及甲州巴登马六甲河含氨量超标,还有雪州仁嘉隆电池厂泄铅,邻近新村受毒害等,皆是在金金河化污事件爆发后所发生。依据气候变化及环境部去年9月所发布的2017年水源研究报告,全国的472条河流中,仅有一条河流,即柔佛杜康峇都河被列入第5级极度污染级别,或俗称的“死河”,河水不能进行任何用途,包括饮用、休闲及灌溉。
短短5个月后,该部部长杨美盈接受媒体专访时却坦言,国内被评为“死河”的河流已增至25条,其中16条位于柔佛州、5条在巴生、槟城及马六甲分别有3条及1条,另有7条河流被列入第4级别的污染。
从而可见,尽管社会开始关注,政府有意加强执法,杜绝河流及水源受污染情况恶化,仍面对著好些阻力,如不法业者以“打游击”的方式随机“投毒”,执法单位难监控等。
从事水源研究的工艺大学教授莫科达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除了不法业者随机“投毒”,现有法律存有的漏洞,也让不负责任的业者得以投机,在合法的情况下毒害河流。

无法将厂方定罪
政府虽已针对工业废水的化物质浓度(mg/l)设下标准,但这些标准仍存漏洞,他举例在《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下,政府监控厂商排出的污染物质,皆以浓度为标准,但其实以污染物质的容量(loads)为标准,才是理想。
他解释, 污染物质的容量是以污水流量( flow ) 乘以污水浓度(concentration)而得(容量=流量*浓度),若只检测浓度是无法计算出废水整体的污染质含量。
“打个比方,若一家工厂依循环境部的重金属质浓度标准排污,但,要是该工厂排出污染质液体流量高,这就会提升污染质在河里的含量。”
他指现有法令下,工厂无论是排放多少的有毒物质,只要浓度低于触法的界限,还是符合规格,可是有毒物质的浓度虽然不高,同样会造成河流污染。
“尽管我们算出一些工厂排放污水污染质容量高,也无能为力,明知厂方排入大量的污质,依然不能将其定罪。”
鉴于此,他认为,立法者应从更科学的角度拟定法令修订案,将检测工业废水的标准,从“浓度”换作“容量”,当然加强刑罚及确保背后涉及者难逃法律制裁,也是修订法令所需概括的。

不法业者省成本 河流投毒难防范
夜深人静时,运载废料的罗里从工厂离开,前往郊外偏僻地区,将工业废料或废水倒入河流,尽管隔日一早,下游的居民发现河水有异,但已无迹可寻。
大马自然协会署理主席周国球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除了厂方有意或无意地泄毒,乃造成河流污染的原因外,河流投毒者是让人最难以防范的。
他说,不法业者选择以投毒方式处理工业废料或废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了方便及节省成本,二则是相关人等为非法工厂,所以更肆无忌惮。
“一些厂方为节省数万至数十万令吉的过滤及处理污水成本,不惜破坏环境素质,将工业废料包括含有化学物质的污水倒入河里。”

周国球也透露,绝大部分将废料倒入河的厂方,皆有相同的习性,即夜间行事,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排出污烟污水或将废料载至偏僻的地方倒入河流。
“此类厂商多数未依循环境部制定规格,安装污水处理系统,也不愿付费给合法污水处理厂进行过滤,以至于采用‘夜间倒河’的方式。”
至于无执照的非法工厂,他指因为无需更新执照,也无需环境部的审核批准,所以情况更加无人管、无人追究,为所欲为。”
然而,他表示,其实对付这些不法业者,政府早已有明文规定,只是业者没依循,政府也没执法。
“有上述种种非法及偷鸡摸狗的行为,皆是执法单位无无行动、无执法所滋长的歪风,若有关单位继续无动于衷,违法的人将继续违例,并且会越来越肆无忌惮。”

滤水站接连关闭 民众饱受制水苦
除柔州金金河化污事件,导致有民众急性中毒外,其他的毒河事件虽未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有人中毒,但已造成数万人因滤水站关闭,而面对制水之苦!
如今年3月4月初,柔州文津河及柔佛河因含氨量超标,先后导致新邦令金滤水站、沙翁第一、第二滤水站、芒加滤水站、柔佛河滤水站及泰丰滤水站被逼关闭,影响逾8万人。
接著在4月中,上霹雳的雷河验出含砷量超标,疑造成下游村民罹患皮肤病,国家水务委员会也勒令关闭附近的阿亦甘达滤水站,令甘榜阿亦甘达的逾千名村民每日皆需等待水槽车前来派水。
同时,最近甲州疑泥鳅鱼池的废料排入巴登马六甲河,导致河水氨含量超过卫生部制定标准,即3.5毫克,当地的滤水站也被逼暂时关闭,影响亚罗牙也约1万8000人的水供。
另一方面,除了急性中毒及制水等直接性影响外,若我国毒河的情况依然未有改善,人民长期接触含有害物质的空气、水和食物,也存有慢性中毒的风险,包括导致患癌、神经及免疫系统等损害及诱变因素,对后代也产生影响。

电池厂泄铅 村民对环境局很失望
正当全国的焦点皆落在柔州金金河时,位于雪州的仁嘉隆新村也同样传出邻近的电池厂疑泄毒,造成沟渠的水源铅含量过高。
“我们好奇,这新村的大沟渠以往有小鱼自在地游水,村民闲时也会前往钓鱼,但在去年杪开始,小鱼不见了,水草也枯萎了,村民感觉不对劲,便开始私下‘调查’原因。”
瓜拉冷岳环保行动协会秘书的温丽婷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透露,本身是一名化学师,也是仁嘉隆新村居民。她与一班村民在去年杪开始收集沟渠水源,送往化验。
“我们新村附近有一家电池厂,据我们收集的资料,该厂的执照是属轻工业,但,我们却寻知厂内竟有热熔铅及磨铅粉等属重工业类型的作业。”
她也说,在化验结果出炉后,发现沟渠水源pH值低,属酸性水质,且含铅浓度也很高,最高达至2.38ppm,村民于是向环境局投报。
“惟环境局前往电池厂视察后,只向居民简单交代已采取行动,未说明所采取的对付行动,包括罚款、是否吊销执照还是暂停运作,该厂也持续运作,依旧排出酸性污水。”
她与村民并非激进份子,但考量到其他村民尤其小孩的健康因素,他们今年2月再次抽取渠水样本化验。
“我记得化验后,再次向环境局投报,对方反质疑我使用的pH探测仪是否符合规格、探测指数是否准确。我是一名化学师,我详细说出探测仪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品牌和其功能,对方立即转换话题。”
同时,她指当局官员当时也拒绝在晚间出动勘察,村民所收集的证据,包括化验报告也不能作为呈堂证据,只要求村民协助继续监督及分享资料。
“这令我十分愤慨,既然我们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他们依然没行动,那么为何还叫我们继续监督?”
此外,随著事情闹大后,厂方虽曾被指示暂停运作,但居民发现该工厂还是如常有排水及员工作业,居民们再次投报、再次向当局理论。她指当时村民的心情,难掩愤慨、不忿及充满失望。
“铅是有毒的,现在我们还未有任何急性症状,但未来呢?我们的孩子呢?我和居民大可不必给自己添麻烦,去抽水样本化验,然后去投报、理论,再后来自掏腰包进行化验……”
温丽婷也说,争取至今,居民们都有些累了,虽然该厂如今已完全暂时停止运作,但当地的人民已对政府机构的诚信及公信力有所质疑。”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